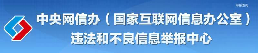摘要:夜郎国是春秋战国时期云贵高原上最大的方国。夜郎国疆域是夜郎文化研究的核心问题,目前学界还没有定论。本文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对夜郎国疆域作一探讨,试图为夜郎文化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借鉴。
关键词:夜郎国;疆域;考证
一、夜郎概况
夜郎国是春秋战国直到秦汉时期位于今贵州西部、云南东部和四川南部的一个较大地方政权组织。《夜郎史稿》认为:“先秦时代在今贵州高原一带的夜郎,是以新石器时代后期进入的越人为基础形成的,战国后期因楚灭越国越人散逃经岭南和武陵地区迁来而得到扩充。”从为数不多的史料可知,夜郎这一政权组织经历了从独立到半独立状态,最后被纳入中央政权的统治之下。其地理位置十分关键,故早在先秦时期就和中原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如《史记·秦本纪》记载:“(秦)孝公元年(公元前361年,即楚宣王九年),……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这里的巴黔中是指曾为巴国之地的黔中。《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巫。庄蹻者,楚庄王苗裔也。”由于楚国在南方开始崛起,先秦时期中原地区与夜郎的联系开始被楚国所取代,楚国位于夜郎地区旁,故夜郎与荆楚的关系也比过去和中原地区的关系更为密切。
《史记·秦本纪》记载:“三十年,蜀守若伐楚,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在楚国收复夜郎不久,被秦再次夺取,将势力伸入到了今川黔滇境。“且兰既克,夜郎又降,而秦夺楚黔中地,无路得反,遂留王滇池。”由于庄蹻的归路被秦阻断,后只得留守在当地,自立为王。夜郎在秦楚争夺黔中郡的时候尚是独立的政权,在庄蹻克且兰,夜郎投降,这一时期的政权是处于半独立结构。“秦并蜀,通五尺道,置吏主之。”秦始皇统一了中国后,在夜郎设立了县,政权半独立的状态便不复存在。到了汉武帝时期,唐蒙通夜郎,设立犍为郡,夜郎接受了朝廷的王位封号,政权一定形式成为了半独立状态,一直到夜郎王兴被牂牁太守陈立所杀,夜郎这一国家才不复存在。历魏晋南北朝、隋唐一直到宋都北只有夜郎郡县的设置,宋代的新晃县设,这也是历史上最后一个叫夜郎的县名。
夜郎国的疆域,古代有关文献记载都不大清楚,只有简单的记载,所以对于古代夜郎的疆域范围至今学界尚无定论,而夜郎国疆域的考察,无论何种观点和角度,必须立足于材料,一则为古籍文献,二则为考古文物,研究必须重视王国维先生的“二重证据法”,因此从古籍文献和考古文物两条研究路径进行考究,几乎是研究夜郎最重要的路径。
近十年来,由于缺乏现存文献及相关考古遗存的佐证,学者对夜郎的研究热潮逐渐消退,相关研究似乎也进入到困局之中,本文就立足于夜郎疆域研究情况的分析,从史籍文献与考古发掘两个方面来进行探析,试探寻夜郎疆域研究的瓶颈之所在。
二、立足于史籍文献的研究
早在建国初,夜郎作为贵州古代历史的重要阶段,相关史料整理与收集便已拉开序幕,直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侯哲安教授在一次考古训练班上介绍了其收集整理夜郎文献的情况,这成为贵州夜郎研究的破题之举,夜郎研究者们便立足于相关文献进行研究。1978年三月份举行的夜郎问题讨论会上,与会者更是从历史地理学、考古学、文献学、民族学等视角,根据文献记载对夜郎的疆域等问题做了讨论,会后出版了《夜郎考》讨论文集之一。
就研究者来看,夜郎研究的古籍文献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中原王朝的汉文献(王朝正史),另一方面便是民族史志的记载了。就汉文献来看,自然以最早也最具权威性真实性的司马迁的《史记》为主,其次是《汉书》、《后汉书》、《华阳国志》、《水经注》等,史籍中关于夜郎的记载虽然简略,但一些研究者仍立足历史文献资料记载推定了夜郎的疆域范围,如杨中兴在《谈谈古夜郎国的版图》中大量运用《元和郡县志》、《水经》、《太平寰宇记》等古文献论证了古夜郎国的疆域范围“不仅据有贵州全省,北和西北还包括川南、滇东北地区;南抵今广西田林、南丹一带,东面到湖南新晃,西至云南曲靖、陆良。”
对于史籍中夜郎国的历史存在,已无质疑,对于“国”的理解也有着一样的共识,即非政治学中的国家概念,也不同于古代分封制下的诸侯国,只能是看作类似于古代所谓的邦国。但学界对于夜郎疆域问题却有着不同的观点,即“大夜郎国”与“小夜郎国”的区别。司马迁的《史记》首次记载了夜郎国,作为亲历西南地区的汉代史官,司马迁对夜郎的描述应该是准确可信的,特别是在《史记》中记载的与夜郎有着莫大关系的滇国在实际的考古工作中得到证实,滇国王族墓葬在云南滇池地区出土,其中还发现司马迁所记载的滇王金印。由此,人们不唯更确信夜郎国的存在。
按《史记》的记载:“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在论述大范围时,司马迁都是以“西南夷”来代称,可见在司马迁看来,夜郎国与周边的君长是有着明显的自主性的,而后至刘宋范晔的《后汉书》则有所不同:“西南夷者,在蜀郡徽外。有夜郎国,东接交阻,西有滇国,北有邓都国,各立君长。”在范晔的笔下,原南夷范围基本尽为夜郎国的属地。这也就有了“大小夜郎国”的区别。
清代有“西南大儒”之誉的学者郑珍在考证夜郎历史时也肯定了大夜郎国的存在,他认为“其域中又必含有三代时诸南蛮小国”。当代学者持此论者甚多。当然,也有研究者不赞成大夜郎国,认为夜郎只是一个族称,不具有“国”或政权含义。还有人认为是史籍记载的失误导致了后人在研究中误认为有“大夜郎国”的存在,禹明先在《贵州夜郎史研究中需要深入探讨的几个问题》中认为:“范晔《后汉书》所划定的‘夜郎国区域’是西汉元光五年以后西迁的犍为郡区域和晋代的犍为郡区域,而不是西汉建元六年所设的犍为郡区域。”这也导致了后来学者把川南六属和成都西南这一广大区域看作夜郎国的范围,研究者通过史籍解读,从而产生了“大夜郎国”的概念。
夜郎疆域研究中,《水经注》、《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货殖列传》、《汉书·地理志》、《后汉书·郡国志》等是记述夜郎最原始的文献,也是我们研究夜郎历史比较可信的第一手资料。尽管涉及夜郎记载的书籍不少,但所记史实均很简略和分散,如除去重复的内容,其文字也不过数千字,涉及历史事实简单,有些甚至相互抵悟,再加上其中魏晋以后的著作,其远离古代,或沿用旧说,或创为新说,旧说则不足道,新说则不足信。仅有的第一手可信史料的局限,大大束缚了夜郎研究的进程。
在汉古籍史料局限的情境下,部分学者产生了夜郎古文献的研究似乎已经穷尽的想法,地方民族史志则给了研究者新的研究思路。就目前所知,在贵州现存的少数民族史志里涉及到夜郎的部分较多,尤其是彝族文献极具代表性。一是散见各书,诸如《西南彝志》、《彝族源流》、(六祖纪)等,均有专章或专节记载。一是夜郎史事的专书,《夜郎史略》、《夜郎史传》和《夜郎斯器》等彝文文献便是其中代表。部分学者根据这些散记和专载,从另一个角度认识夜郎,也为探究夜郎疆域范围提供了新途径。
值得一提的是,研究者对民族史志的解读成果中,1998年8月贵州民族学院王子尧刘金才主编的《夜郎史传》极具代表性。该书系家传彝族手抄本古文献,全书对夜郎的源流、疆域、谱系、政治、经济、军事、战争等做了详细记述。《夜郎史传》是研究者利用少数民族文献进行夜郎研究的首部著作,对于后来研究者利用研究民族史志进行研究提供了新思路。此外,《夜郎史稿》、《夜郎研究述评》等相关著作也进一步阐释了夜郎的历史进程、势力范围、社会性质等。
而从已出版的相关成果来看,部分研究者通过解读彝族史志文献,推断出夜郎大体上可以分成武米时代、佐落举时代等四个时代,其疆域大小、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中心,随着各个时代的变化也不断变迁,简而言之,夜郎的疆域也并分静态不变,而是动态变化的,太史公笔下的“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中的夜郎也许正处于其疆域管控的较大范围,其地望始终跨今贵州、云南和四川三省,最大时北达成都,越安顺西及昆明(今曲靖),东抵贵阳,故有“大夜郎国”之称。
但是,研究者对民族史志资料的解读与运用却有着难言之隐。一方面,史志中记载夜郎的资料虽然丰富详细,但由于缺乏少数民族文字研究学者,绝大多数的资料未翻译整理出来并作系统的辑录研究,也就更谈不上做好系统的文献谱系的梳理工作,学界仅有的几篇成果也仅就现已翻译了的有限资料做出的研究,另一方面,虽然民族史志给了研究者新的文献研究视野,但地方志与民族史志的可靠性还有许多存疑之处,尤其是很多民族史志经过历史风云激荡,其内容也许几经更改,并不能认作是具有国家正史性质的具有较高可信度的史料来看待,有些则是古人神话传说的记载,也不能证明是原住民的现实记载,所以,对于民族史志的运用研究要审慎对待。
三、考古发掘的研究路径
长期以来,人们对于夜郎疆域问题的研究一直侧重于史籍文献,但是史籍文献对于夜郎疆域的记述简略而又分散,更加上有些史籍前后相抵触,夜郎疆域的研究也就不免陷入无根之水的境地。为将相关研究更加深入,将史籍文献与考古发掘相结合是必要且必须的。
1980年,“夜郎考古”作为单一命题在贵州省文物局与社科院组织的夜郎研讨会上明确提出,但直到1995年贵州省政府批准成立贵州夜郎考古工作领导小组,贵州夜郎考古工作才得以系统开展,从五十年代至今,滇黔各地考古调查和发掘获得的夜郎时期文物总数已逾千,其中最值得重视的是贵州普安铜鼓山、赫章可乐及威宁中水等三个地点古遗址与古墓群的发掘。这三个考古遗址发掘出土文物最丰富,地方特征也最突出,但分布也较为分散,正如梁太鹤先生在《夜郎考古思辨与述评》中认为:“普安铜鼓山被较多研究者认为在狭义夜郎地域内。赫章可乐被认为是汉武帝开西南夷后所设汉阳县地。威宁中水或以为属汉代朱提县地,或以为亦属汉阳县地。虽均为史载‘夜郎旁小邑’,但仍在广义夜郎范围内。”
研究者立足于相关的史籍文献,结合考古发掘成果,对夜郎的研究做出了有力的推断,大都认为夜郎的主体应是在贵州,但是其控制的疆域范围却横跨川滇黔三省,如李洪涛在《古夜郎国疆域研究》结合史籍与考古资料,认定夜郎的疆域范围:东为遵义市、贵阳市、安顺市、黔南州、黔西南州、毕节地区、六盘水市,西为云南的昭通地区、曲靖地区、文山州、红河州,南为广西百色地区的北部,北为四川的宜宾地区。当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夜郎处于“君长”林立的西南夷地区,其地域疆界必定是动态变化的,研究者如一味想确定夜郎疆域的固定范围,则是弃本逐末,难以实现。
在具体研究中,考古资料的运用对论证夜郎大致的活动范围是起着证史的作用,研究者要谨慎仔细采选,且要审慎看待夜郎考古成果。就以贵州夜郎考古发掘来看,成果是较为丰富的,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贵州已陆续出土过一批战国至汉代颇具特色的文物,包括磨制石器、骨角器、陶器、铁器与铜器。这些文物基本分布在贵州西部地区,属古代大夜郎国的地域范围。学界如何定性这批文物是至关重要的,这对于推断夜郎疆域也是要面对的问题,研究者应仔细看待。
就目前夜郎考古研究来看,夜郎地区青铜文化考古由于地域性不够广泛,典型的遗址、墓葬等发掘太少,尚不能代表为典型的夜郎文化进行解释与推断,云贵等省市考古工作也没有挖出来更多的遗址,而已经出土的有文字的考古材料又缺乏精到的分析,换言之,也就是缺乏做战国秦汉铜器铭文与出土文字史料方面的人才。另外,虽然现在已基本建立了黔西北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的文化序列后,但是先秦时期文化序列仍是空白,为此加强几大流域的考古调查,选取典型遗址进行发掘,以解决川黔滇等地区考古材料排序、分期和年代问题是紧迫的,而这将对夜郎疆域等问题的研究提供助益。
四、结语
生活在南中地区的“夜郎”,在考古上至今还是一个空白,因此,搞清楚夜郎的疆域范围、地理位置,是当前贵州省学术界和考古工作中较为迫切的任务。本文宗旨是就夜郎疆域研究的两条路径进行分析,从而探究出夜郎疆域研究的瓶颈,通过对疆域研究的梳理,我们发现瓶颈的核心是史料局限,具体有以下两点。
第一,就文献史料来看,正史上的史籍材料简略而又分散,其中有些内容甚至相互抵悟,根本来说,相关汉文献没有更多空间,民族史志虽开辟了夜郎研究的新思路,但是民族史志没有做好文献谱系的梳理,相关的史料也有许多存疑之处。这些瓶颈大大局限了夜郎疆域研究的进程,研究者想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则需正视这些问题。
第二,考古发掘方面,专业考古人员的短缺,尤其是独当一面的考古领队的缺少,使得相关的夜郎考古缺乏聚落材料,而已经发掘的夜郎考古遗址,由于地域性不够广泛,典型的遗址、墓葬等发掘太少,难以作为典型的“夜郎文化”进行研究,再加上,有文字的考古材料又缺乏专业人才进行精到分析,考古材料排序、分期和年代问题的空白也是局限夜郎疆域等问题进一步得到解决的瓶颈。
长期以来对于夜郎的相关研究都莫衷一是,但不代表夜郎疆域问题的研究就此陷入困境,随着各学科的发展,为应用多学科综合比较的方法来解决夜郎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多学科交叉研究具有相互印证、相互补充等优越性,我们应该把握住夜郎研究的重心,努力克服研究中出现的瓶颈,为求将夜郎疆域研究的进程进一步深入,从而不断认识夜郎文化,早日解开夜郎之谜。
【作者介绍】:周 艳,贵州大学,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
(编辑:陈斯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