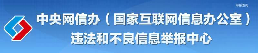文/赵金禾
有位叫朱红兵的作家朋友,写了篇文章叫《金禾笑赋》,翻译成白话,就叫金禾的哈哈。令人忧伤的是,他已经去了另一个世界。他的作品还在。搞文学的一个好处,就是他的作品比他的人活得长。
认识我的人,接触我的人,大约是不会忽略我的笑声:哈哈。有人公然就叫赵哈哈,以至在开某个不大不小的会议上,主持人点名:赵哈哈来了没有?没有人不知道是我的。
我开会爱迟到,或者干脆不到,到了就坐在角落里看书,或在我专属的写作小本子上写什么东西,别人还以为我是在做会议记录呢。
上班的时候,同事说起什么事,我总是爱笑,打起哈哈笑。楼上组织部的人说(那时我在楼下宣传部工作),赵哈哈人没进门哈哈就进了门。
我的同事一个个被提拔,总是没有我。我假装不计较,朋友们为我鸣不平。有位接近领导层的朋友说,你知道你为什么不能被提拔么?我打起哈哈,像模像样地洒脱说,那不是我关心的事哦。
朋友说,你别跟我打哈哈了,你害就害在打哈哈!
我仍是哈哈。朋友严肃又不乏机密地说,你总是一个哈哈打破天,像入无人之境,毫无顾忌——告诉你:领导不喜欢!领导认为这是不成熟的标志!你能不能改一改,少打些哈哈或不打哈哈,忍一忍不行吗?
朋友语重心长,我有所感动。忍一忍就忍一忍,这有什么难的。我忍着十天不再打哈哈。许多人不解:赵哈哈是怎么啦?
有位十多天没见我的朋友见了我大吃一惊,说我是不是病了一场?怎么像是人小了一圈,眼睛大了一圈?我回家照镜子,果然一个好端端的赵哈哈,有了让我不能接受的异样。
我还忍什么呀忍?去他妈的。我跑到河边树林子里,疯狂地打起了哈哈,笑我痴,笑我傻,笑我把自己忍死了人家还不知道我是怎么死的。
赵哈哈还原了赵哈哈。重获自由了。
朋友王昌波调到宣传部当了部长,我请他将我调到文化馆搞文学。他说,怎么我调来了你却想走?不够意思了吧?我说如果你还是我的朋友,就放我一马。他说让他考虑三天。结果他只考虑了一天就放了我。
那时候文化馆的馆长归组织部管,他说委屈我,只能让我暂时当副馆长负全面责任。我说怎么都行,只要放生。有位朋友见了我总是喊我赵馆长,我说你要么就喊赵金禾,或喊赵哈哈,或喊赵副馆长。我们一起哈哈大笑。以后他见了我,很规范地喊我赵副馆长,我更正说,我现在是赵正馆长了。我们又是一起哈哈大笑。
我在文化馆工作了十年,因为我没丢掉我的写作,像没丢掉我的哈哈一样,极力鼓励文学创作的原地委书记(不知是不是副的,我一直没去搞清,好在这不重要)唐玉金喜欢我的文学激情,也喜欢我的哈哈,极力说服县里组建文联,让我去文联工作。
那时候的风声,是不再组建县里的文联机构,要组建只是内设于宣传部(如云梦)。我不知唐书记走了哪条路子,安陆居然被批准单设文联了。我去任了常务副主席(主席是宣传部副部长兼任)。
我在文联工作了又一个十年。我的哈哈声更响了,有人说赵金禾哈哈比他的作品更有名。这样形容我的人是个天才,因为他认可了人的本真。
结束本文之前,想挑明一下金禾哈哈是一种语言的多重意味:有豪放,有宽厚,有轻视,有自嘲,有乐之悦之取之舍之爱之,还有自知人不知,或人知自不知的混沌啊。
(编辑:陈斯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