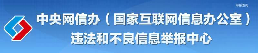“外婆走后的第三天,窗台上的栀子花开了。我数了七朵,三朵朝东,四朵朝西。”
雨还在下。细细的,绒绒的,黏在玻璃窗上,汇成一道又一道溪流。梧桐叶子湿漉漉地亮着,偶尔一辆车碾过积水,那声音也闷闷的,像一声被捂住了的叹息。
屋里太静了。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一下,两下,擂在空旷的胸腔里,有点慌。空气里浮着一种旧木家具和雨天气味混合的凉意,吸进去,肺腑都像被清水涤过一遍,干净得发空。
我转过身,目光无神地扫过客厅。沙发是老式的,铺着素色暗纹的垫子,扶手上搭着一条褪了色的薄毯。茶几上,一只白瓷茶杯静静地搁着,杯沿内侧有一圈极淡的茶渍。一切都还在原位,仿佛主人只是暂时离开,马上就会回来。
我走向卧室。脚踩在地板上,发出轻微的吱呀声。卧室更暗一些,窗帘半掩着,滤进的天光是灰色的。床上铺着平整的灰黑格子床单,枕头蓬松,没有一丝褶皱。这里的时间似乎走得更慢,尘埃的沉降都小心翼翼的。
就是在那扇老旧的窗户前,我停住了。
窗台很宽,是老式楼房才有的那种。此刻,一片素白撞入眼帘。
那是一盆栀子。栽在一个朴素的陶土盆里。叶子绿得深沉,油亮亮的,仿佛把窗外所有的阴翳都吸了进去,淬炼出根茎那沉静的墨色。就在这墨绿的底色上,开着花。
我下意识地开始数。一朵,两朵……七朵。不多不少,七朵。
它们开得毫无征兆。昨天?还是前天?记忆里还只是一簇簇紧紧包裹的青白花苞,沉默地隐在叶间。怎么一夜雨过,就全都坦然地绽开了?花瓣是厚重的白,层层叠叠,边缘有些微的卷曲,像古典仕女裙裾的滚边。花心处,是一小撮更密集的、鹅黄的花蕊。被雨气浸润着,那便不仅厚重的白,是莹润的、凝脂般的白,仿佛自身就是一个柔和的光源,在这昏暗的室内,幽幽地亮着。
看得久了,我注意到它们的方向。不是散乱地开着,而是有着微妙的区别。
三朵,稍稍朝向东面。那是城市日出的方向,尽管此刻被层云和楼宇遮挡。另外四朵,则微微倾向西边。西边有什么呢?更远的郊区,蜿蜒的河流,再往西,便是连绵的矮山,以及山后,我来的方向。
外婆是三天前走的。安静地,在睡梦里。母亲在电话里的声音干涩得像深秋的落叶,她说,没有痛苦,就像一盏油灯,慢慢地,燃尽了最后一滴。
之后我匆匆收拾行囊,踏上归途。一路上,车窗外的风景飞速倒退,绿色由疏淡变得浓稠,再由浓稠变得陌生。我是在这里出生,长大的,可十八岁以后,便像一枚被风吹远的种子,落在遥远的城市,生根,发芽,努力适应着另一片土壤的酸碱。故乡成了地图上一个熟悉又疏离的坐标,只有年节时,才被短暂地标注。而外婆,是这坐标上最温暖、最恒定的一点。
现在,这一点熄灭了。
葬礼简单而肃穆。亲戚们来了又散,安慰的话说了又说,像潮水漫过沙滩,留下湿漉漉的痕迹,又很快被风吹干。母亲和姨妈们收拾遗物,商量着哪些该留,哪些该处理掉。屋子里的空气忙碌而滞重,悲伤被具体的事务切割成一小块一小块,反而让人得以喘息。
外婆留下了这房子,这家具,这盆花,留下了无数关于她一生的记忆碎片。但她的人,确确实实地“去”了。而我,年年月月,也一直在“去”与“留”之间辗转,可每一次的“留”,都让我更清晰地意识到自己早已是个“离去”的人。
雨似乎小了些,变成了更缥缈的雾状。一朵朝西的栀子,最边缘的一片花瓣上,聚起了一颗极饱满的水珠,颤巍巍地,悬而不落。那水珠澄澈透明,将窗外颠倒的、灰蒙蒙的世界,静静地盛放在里面。然后,毫无征兆地坠落了,沿着花瓣的弧线,悄无声息地滑落,隐入下方的叶丛,不见了。
就在那一刻,我忽然闻到了。
之前全副心神都在看,在想。直到这动态的一瞬打破凝望,那香气才猛地攫住了我。它早就弥漫在空气里了,只是我迟钝的感官刚刚才向它敞开。清冽的,带着雨水的润和植物根茎的微苦,一丝丝钻进鼻腔,沉入胸口,将那淤塞的空洞一点点填满。成为一种无比坚定、无比柔和的存在。
七朵花。三朵朝东,四朵朝西。它们就这样静静开着,不为什么,不证明什么,也不回答什么。生的,便这样生着。以一朵花的形态,以一阵香气的形态。
逝去的呢?真的就无形无迹了吗?那这满屋子的静默里,为何我能触摸到一种熟悉的温度?那薄毯上的褶皱,那茶杯里的茶渍,那空气中仿佛还未散尽的一声轻唤……它们不是实体,却比实体更顽固地“存在”着。它们“留”了下来,留在物的记忆里,留在我的记忆里,留在这盆绽放的栀子,那无言却磅礴的生命力里。
我深深吸了一口气,那清冽的香仿佛有了实质,充盈了四肢百骸。窗外的梧桐,叶子在微风中轻轻晃了晃,抖落一串细碎的水光。
去,是必然的。留,是永恒的。人一辈子都在离去的路上,而比离去更令人难以释怀的,是被留下。
我最后看了一眼那七朵素白的花,转身,轻轻带上了卧室的门。客厅里,母亲不知何时已经醒了,正坐在沙发上,手里握着那只白瓷茶杯,望着窗外的雨幕出神。我走过去,挨着她坐下,没有说话,只是加入这满屋的沉默。
雨,快要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