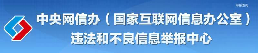那天下午,我站在即将拆迁的老街尽头,看着夕阳给斑驳的马头墙镀上最后一层金箔。空气中飘着旧木头受潮的气味,混杂着谁家飘出的、稀薄的炊烟。
就在一堵即将倾颓的灰墙下,我无意间踢到一个半埋在碎瓦中的物件——那是一只粗陶的蟋蟀罐,罐身早已磕破,露出的内壁,透露出温润的、被摩挲过无数次的光泽。
我细细拂去尘土,罐底竟还留着一层干涸的、极细的黄土。恍惚间,我仿佛看见许多个夏秋之夜,就着昏黄的灯火或清朗的月光,一只油亮健硕的“将军”在罐中振翅,发出断断续续的“瞿瞿”声。这声音曾是一个街坊、一个院落、一整个时代里,最寻常又最精微的听觉注脚。孩子们将脸颊贴在罐壁上感受那震动,大人们则在鸣声里默想着自己的心事。这便是一种宁静的浪漫——一种将漫长时光,温柔地浪费在无用而美好事物上的奢侈。
我摩挲着粗陶的裂纹,似乎,我们已经失落了太多这样的浪漫。
我们失落了星空的浪漫。祖父辈的人,能在庭院里凭星斗的位置判断时辰,能指认银河两岸的传说,能从“七月流火”的轨迹里读出季节那细微的转身。星空对他们而言,是一幅巨大、幽深、且与自身命运隐隐相关的画卷。而我们的夜空,常被辉煌的人间灯火漂洗成一片空洞的暗色。偶尔抬头,即便看见几颗寥落的星子,也多半叫不出它们的名字。我们与星辰之间那份古老、神秘、私语般的联系,早已被切断。星空不再是一个引人思忖的浩瀚剧场,它退缩成了一种遥远的天文现象,一种手机软件里可以随意调取、却不再触动心弦的数据图像。
我们也失落了等待的浪漫。所有的“慢”,好像都成了一种急需矫正的缺陷。食物的滋味,不再关联着从播种、生长到炊煮的漫长序曲;一份资讯的价值,似乎也仅在于它被获取的“第一秒”。木心先生怀念的“从前慢”,那种“车,马,邮件都慢”的节奏里,酝酿着的是在时光里自然发酵的醇厚情感。如今,即时通讯将思念压缩成扁平的文字与符号,随时可达,也随时可被覆盖、撤回或忽略。我们消灭了距离,也一并消灭了距离所滋养的望眼欲穿、辗转反侧与刻骨铭心。没有了“长久的等待”这层底布,“抵达”所带来的欢愉,也显得单薄而廉价。
我们更失落了“物”的浪漫。我手中的这只蟋蟀罐,是一名匠人手指的温度与泥土对话的产物。它被创造出来,是为了承载一个秋夜的生命,参与一场天真的游戏。而今天,我们被淹没在完美、光洁、标准化的工业制品中。它们高效、实用,从流水线上成千上万地涌现,满足我们层出不穷的欲望,却在欲望满足后,又迅速沦为电子垃圾或时尚废品。我们与物的关系,变得直接、功利、毫无留恋。物所承载的“故事”越来越少,所铭刻的“记忆”越来越薄,不再是与我们生命时光共同呼吸、慢慢“养”出温润包浆的伴侣。我们占有一切,却又不曾真正拥有过任何东西。
那么,这逝去的浪漫,究竟流向了何方?
它或许并未彻底消亡,只是在我们日益高效、精明、目的明确的生活里,悄然退居到了意识的边缘,成为一种“怀旧”的素材,或一种“小确幸”式的偶然点缀。我们会在某个疲惫的间隙,突然渴望一场毫无目的的散步,或盯着窗外的雨滴发一会儿呆——这未尝不是那宁静浪漫,在心灵深处不甘的、微弱的躁动。
只是,当这种挣扎越来越稀薄,当我们的心灵被越来越多的“即时满足”与“有用之事”填满,我们是否会变成一种更加贫乏的存在?一种虽然链接万物,却难以与一片星空、一阵虫鸣、甚至一件旧物产生共鸣的存在?我们不知道答案,也少有人去寻找答案。
思忖良久,我最终带走了那只残破的蟋蟀罐。它再也无法装下任何一只秋天的蟋蟀。但或许,它可以作为一个渺小的证据,提醒我自己,我们曾经那样生活过——缓慢地、专注地、充满温情地与这个世界相处,在那些看似“无用”的时光与陈旧物件里,安放过我们饱满而宁静的灵魂。
老街终将被推平,将之取代的,是崭新的、齐整的、闪着玻璃光泽的建筑。效率与繁华将覆盖一切。只是,当最后一段关于蟋蟀鸣叫声的记忆也消逝在风里,我们迎来的,究竟是一场进步的凯旋,还是一次无声的、关于浪漫的告别呢……
也许,我们需要在这个感情趋近于儿戏,生活愈发无暇喘息的时代里,尝一碗小火慢熬的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