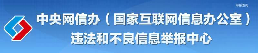《乡土中国》是费孝通著述的一部研究中国农村的作品。首次出版于1948年。
全书由14篇文章组成,涉及乡土社会人文环境、传统社会结构、权力分配、道德体系、法礼、血缘地缘等各方面。在《乡土中国》中,作者用通俗、简洁的语言对中国的基层社会的主要特征进行了概述和分析,全面展现了中国基层社会的面貌。全书主要探讨了差序格局、男女有别、家族、血缘和地缘等。
《乡土中国》是学界共认的中国乡土社会传统文化和社会结构理论研究的重要代表作之一。
贺雪峰的《新乡土中国》,广西师大出版社2003年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修订版。全书分乡土本色、村治格局、制度下乡、村庄秩序、乡村治理、乡村研究方法六篇共64篇文章,对农民和农村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解读。作者从乡村生活的细节——诸如半熟人社会、农民的合作能力、村庄精英的谱系、农民负担机理等等作深入透视,让读者沉浸到乡村中,冲击原有的对乡村的经验与想象,促使你去思考,这正是不易察觉的中国经验、中国常识。
贺雪峰,1968年6月生,湖北荆门人,法学博士。长期从事农村调查,自1996年以来,先后在全国二十余省市做农村调查,调查内容涉及村民自治、乡镇财政、乡镇选举、信访制度、税费改革、农地制度、建设用地制度、乡村水利、农业经济、农业现代化、农民福利、农村文化、农民宗教、乡村社会性质、农村弱势群体、新农村建设、农村扶贫、乡村规划、农民工、城乡关系、城市化等等方面,2002年至今一直主持湖北六村乡村建设实验,累计驻村调查时间超过1000天。
贺雪峰教授所带领的学术团队长期致力于农村研究,主张“田野的灵感、野性的思维、直白的文风”,以他为核心的研究团队被称为“华中乡土派”。
2017年12月,贺雪峰教授正式就任武汉大学社会学系主任。
2019年,任武汉大学社会学院首任院长。
发表学术论文一百余篇,出版著作十余部。
读了该书,与财税史有关的话题我特别关注。
一是农业税。
村干部除了协助县乡向农民收取税费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工作是为单家独户农民提供“一家一户不好办和办不好”的公共事务,其中向农民收取税费中,包括农业税、“五统”、“三提”和共同生产费,其中农业税交给国家,“五统”交给乡镇,“三提”留在村集体,共同生产费用于村社集体共同生产事务。一个村庄,收不起来农业税,缴不上“五统”,当然也不可能有“三提”收入和获得共同生产费。而离开村社集体,“人均一亩三分,户均不过十亩”的农民不可能独立解决共同生产事务,因此出现了农业生产环节的各种困难,甚至村民之间的正常关系都难以维系。一个强人村干部不仅可以协助乡镇向农民收取农业税,而且可以收上共同生产费从而为村民办成他们“办不好和不好办”的生产和生活中的各种公共事务。
以上两端,就在村庄中形成了十分独特有趣的好人治村与恶人治村的循环。
取消农业税后,国家不再向农民收税,且取消了面向农民的各种收费。甚至用于共同生产事务的共同生产费也不再允许收取,而代之以“一事一议”筹集共同生产费用。“一事一议”要求就每一件村集体要办的公共事务,由村民代表讨论由村民按受益程度分摊费用。实践的结果是,全国绝大多数农村“一事一议”都搞不起来,农村公共事务就不再有资金来源。
取消农业税后,国家不仅不再向农民收取税费,而且向农村转移大量资源。转移资源的办法有两种:一是粮食补贴、种子补贴、综合补贴等资金直补到户,一卡通;二是通过条条自上而下转移,以项目制的形式建设农村公共品。
项目制是由乡村申报,由部门审批。村干部必须要有关系,要善于跑项目,才可以获得上级转移资源进村。村干部跑来项目和资源是村干部的本事,与村民无关。不过,村民可以从项目中获得好处,因为这些项目都是惠农工程。因为农民并无付出,又可以得到好处,村干部跑来资源是他有本事,跑不来资源也没让村民受损失。这样一来,村干部向上级跑资源就逐渐与村民没有关系,在自上而下通过条条转移资源的过程中,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个新的县乡村利益共同体,这个新的利益共同体与过去的不同,就是这个新利益共同体没有自我爆炸的机制,是可以持续的:只要上面有资源转移下来,这个利益共同体就可以越结越厚,越养越肥。经过这个利益共同体,无论中央转移下来多少资源,农民都很难获益了。
如何打破目前通过条条向下转移资源,通过项目申报来进行惠农工程建设的以上体制性问题,是一个重大难题。
时代不同了,干部职责不同了。
二是大操大办。
由于当前人们经过革命运动和无神论教育,成为彻底的唯物论者,知道人之生死是一种自然现象,并不存在阴阳对话,因此,这种本来是阴阳对话的仪式,也就没有了禁忌和恐惧。没有禁忌和恐惧的丧事仪式就变得不可理解。以前一直如此办丧事的特殊程序和仪式本身不重要了,因为那些特殊程序和仪式只是迷信。没有禁忌和恐惧的人们办丧事的仪式,就不关心阴阳两界的交流,也就是不相信与神和鬼的世界的交流,但这种一直是办大事的仪式却保留了下来。这个时候,若村庄村民之间还有竞争的话,就自然而然地在办丧事的仪式上表现出来,办丧事成为生者与生者之间的竞争。这种竞争可以向两个方面发展。一是恢复传统的仪式,比如竞相请道士念经,但这时请道士念经的生者并不是关心道士念经会给死者与生者带来什么交流,而是别人在丧事上做的事情我也做了。别人请了一个道士,我请两个;别人请两个我请3个。有人一次请10多个道士来念经,念给旁人看。二是借用现代手段,比如沭阳的电声乐队。既然只是生者之间的竞争,办丧事就要办出声势。现代手段的声势更大,与电声乐队震天的音响比,唢呐声音太尖细、太普通。你可以请电声乐,我就再加上唱流行歌曲;你唱流行歌曲,我就表演现代歌舞。总之,作为生者竞争的办丧事,因为失去了人们对死亡的敬畏,失去了对鬼神世界的禁忌和恐惧,而变成了大操大办、不伦不类的“喜事”,变成了外人无法理解的一出闹剧。
婚礼是另一件容易大操大办的仪式。过去通过婚礼仪式,新婚夫妇向众人宣誓,新的家庭组成了,这是一个可以对众人负责任的家庭,也是一个可以稳定预期的家庭。现在,婚礼在城市越来越不重要,在农村也越来越丧失其本来的意义。婚姻成为现代人的私事。因为是私事,目前可以随便地、自由地谈婚论嫁,可以随便地离婚再婚。不是说这样一定就不好,而是说,传统婚礼仪式所表达的社会宣誓组成“白头到老”的对社会负责任的家庭的意义消失了或正在消失。婚礼越来越变成什么呢?变成了收钱和送钱的游戏。今天网上有一文《强迫的悲欢》,是说当前办的红白喜事,请柬满天飞,“八竿子也打不着的灰溜溜的他和她”,也愣要“悲伤着他的悲伤,快乐着他的快乐”,就是要收钱呗!而一个镇委书记3年办9次红白喜事,一个副县长的父亲去世竟大操大办到当地物价上涨的例子,不一而足。
现在有了好的思路。彩礼限高标准如何定?江西多地新探索:按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约3倍算。统计指标有了新功能:平息争吵。
三是分摊负担。
近些年来粮价低迷,农民负担沉重,承包土地这种权利的含金量大大降低,一些农村的农田大片抛荒,村集体能给村民的已经很少了。反过来,村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的开支,上级不断加重的税费提留,村组干部的报酬和村务管理等费用,需要摊到村民身上。有些村民不耕种村集体的土地,不享受村庄的福利,仅仅是有村籍这一项,就得承担这些分摊下来的费用。1999年我在湖北一个有名的豆腐村(钟祥石牌)调查,全村近1/3的村民举家在全国各大中城市做豆腐。村干部到年底,有一项任务便是到全国各地找豆腐郎和豆腐娘们收分摊到他们头上的费用,一年竟可以收10多万元,虽然收这10多万元要花费数万元路费。这就难怪农民会托关系迁走他在本村的户口,这样他就不再具有本村的社会身份,享受不到村民的好处,也不再承担繁重的义务。
田野调查的很细。
四是农业特产税和屠宰税(“两税”)。
2000年到吉林金村调查,发现金村也如荆门农村一样,传统的人际联系正在解体。
从农民负担方面看,金村农民负担也很轻,金村所在乡竟然一直没有开征农业特产税和屠宰税这两项荆门农民最为不满却无可奈何的平摊下来的税收。
从一开始,中央就强调农业特产税和屠宰税(以下称“两税”)应据实征收。但直至今天,大部分农村“两税”仍然是按户或田亩平摊的。按说“税”是很规范的,特别是屠宰税,农民没有杀猪,当然就不应该纳税,杀一头猪,也就应该纳一头猪的税。可是,我们在全国调查,几乎没有农村是据实征收屠宰税的,即使按猪头去征税,也远远超过应纳税额。在江西调查,杀一头猪要据实征收40多元屠宰税,远远超过了实际应纳税额(实际应纳10—12元),据实只是你是否杀了猪,而税额是上级分解下来的总额按猪头平摊。在湖北调查,不少村户平摊屠宰税上百元,有的农户未杀猪也得摊这么多税,这是按户头平摊的,离据实征收更远。
中央知不知道“两税”平摊?知道的,不然中央文件就不会一再强调“两税”要据实征收了。不仅中央知道,“新闻调查”和“焦点访谈”等媒体总是曝光一些地方猪头税变人头税,谁都知道了。谁都知道按人头平摊“两税”是不对的事,却偏偏在全国很多农村平摊了10余年,直到今天仍然如此,为什么?不是因为乡镇“两税”平摊违反中央减轻农民负担的事实不明显,而是“两税”平摊是全国农村的事实,“两税”平摊还未达至农民承受负担的底线,或者说“两税”平摊还未引起恶性案件。有些“点儿低”的乡镇出现了这种恶性事件,其负责人就要倒霉。在农民组织能力较强的地方,“两税”平摊容易引起群体性事件,如我们调查的江西某乡镇,就因为屠宰税平摊引发数千农民闹事。但全国有组织的农民太少,发生恶性案件的机会要等到农民不堪重负到极限才会出现。
农村费改税的目的是为了将农民合理负担与不合理负担分清楚,乡镇只能征收农业税、农业特产税和“两税附加”,其他一律不准征收,农民也有权拒交。但是,以前中央也规定农民有权拒交一切不合理税费,并给每家每户发“农民负担卡”,写上可以拒交一切负担卡之外的不合理负担,而实际上大多数农民都交了负担卡以外的不合理负担,因为拒交不了。明明白白的屠宰税,按户平摊,不杀猪也得交,而且交的税额远远超过杀一头猪所应纳的税。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说费改税之后,乡镇就不会向农民收取税以外的费?有什么理由相信农民有能力拒绝乡镇超过规定的收费?又有什么理由相信费改税后国家就会加大力度查处乡镇一级大量的加重农民负担事件?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不改变农民负担加重的机理,税费改革将会变成治标之策。
没有想到,社会学者如此理解“两税”的。
两税法,是唐德宗时代的建中元年(780年)由宰相杨炎建议推行的新税法。是以原有的地税和户税为主,统一各项税收而制定的新税法。由于分夏、秋两季征收,所以称为“两税法”。
2003年3月,在北京开全国人大会,认识清华大学秦晖教授,他的“走出黄宗羲定律怪圈”之说,极大地推动了免农业税运动。
五是公车。
前些年,乡镇一级财政支出的决定权相对较大,但随之出现的是教师工资长期被拖欠,应该支出的财政资金未能支出,不应支出的财政资金到处都支。就是在1990年代中后期的中西部地区,一方面教师工资被拖欠,一方面乡镇建办公楼、买小车的支出却很多。中部地区乡镇一级无论多么小的一个乡镇,书记、镇长一人一辆专车的情况相当普遍。
为了维持高额的办公费开支(专车支出、招待费支出等),乡镇克扣教育资金、农林水利资金、文化广播资金,已是公开的秘密。不仅如此,乡镇还到处借债务,欠债数千万元。因为乡镇财政该支不支,不该开支的却到处开支的问题实在严重,上级不得不收回乡镇财政支出的权限,先是普遍将教师工资收回县市一级,再是一些地方将公务员工资由县市直达。接下来还会由县市直接下拨乡镇的农林水资金、教育资金,由县市规定乡镇小车使用权限、招待办公费的上限等。逐步取消乡镇财政开支的决定权。乡镇财政节支的积极性事实上也不存在了,因为节支的空间没有了。
我提出“公车相对论”,认为,同样级别的干部,在不同地方,公车待遇不同。处级干部在省直机关没有公车,在地级市直机关就有公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