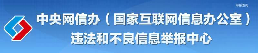田友国
天龙湾
读长江流域先贤陶渊明的诗与赋,我便遥望着他那悠闲漫步,信手采得几株菊花的背影。对于他的诗与赋,以及名高节清,我是默默地读,不出声,唯恐惊扰了这位先贤“不与世相逐”的清静。
长江边的宜都天龙湾国家湿地公园也很清静,这里遍山的桔子压弯树枝,树枝不会叫一声“累”。人把脚伸进清水,会有小鱼游过来。偶有狗吠、猫叫,听上去也是一句纯朴自然的田园诗句。当然,也少不了古诗“鸡鸣桑树颠”的遗绪。宜都天龙湾富含陶渊明诗与赋的意境。我想,如果陶渊明在世,他一定会来到这里,再写出“似大匠运斤,不见斧凿之痕”的诗与赋。
陶渊明以诗与赋的方式还活着。
与南朝宋初相隔一千五百多年,长江流域另一位先贤杨守敬回乡探亲了。他站在宜都天龙湾,穿着清末民初的长袍,左手背在身后,右手执着书卷,以雕像的姿态融入东升的岚气之中,也融入宜都老乡乃至各地游客的景仰之中。
有关杨守敬流芳懿范的事迹,早播于宜都民间。同治元年,杨守敬科举入仕,鼓帆而远,赴任晚清驻日使馆。归国之后,执教于湖北黄冈、两湖书院。杨守敬兼通历史与地理,又博取金石文字、版本目录、书法、藏书诸家,尤其是以七十六岁的生命长度,留下了宏富的著述,完成了八十卷的皇皇巨著《水经注疏》。虽说杨守敬在一百多年前已无疾而终,但他仍然活在他的著述里,活在今人的阅读中。
宜都人民仰慕杨守敬渊博的学识、远扬的声名,在“八百里清江”下游建了一座杨守敬书院。在我看来,这座书院不止是纪念这位先贤,更是文化上的传承。
杨守敬一生远离家乡,穷波探源,高翔遐翥,但血液里流淌着清江的基因,落叶归根是他终极的情感取向。宜都人民懂他,把杨守敬接回家,请他在这座书院讲学。
杨守敬书院背山面水。我步入迎客堂、四宝堂、勤成讲堂,似乎听到了杨守敬对“长江三峡”、“清江源头”的界定,也仿佛听到了宜都后学的读书声。窗外,雨摇竹影,风弄松姿,一派诗意。这情景,恰与北宋东林书院遥相呼应,也切合了一句名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杨守敬书院不远处,有一座长清观。长清观始筑于元朝年间的砚墨山上,后虽风雨蚀颜,香火忽明忽暗,但在宜都人民的虔诚里却绵延了七百三十多年。长清观重修后,殿宇相望,凝山川之灵气,聚天地之精华,是香客向善、养生与祈福的好地方。
长清观另有一景,是一位美丽年轻的女道士。她发髻高绾,穿一袭黑色长袍,举止从容,言谈富有涵养,一身的仙风道骨。这位女道士有本科师范的学历,却把人生前段的故事留在了凡尘,身居长清观修道,清静无为了。她给人以丰富的想象。来到长清观的香客,或许会多看她一眼,然后再举一炷香火祈禳。
长清观与杨守敬书院之间,飘着一条带状的小山道。小山道的一端珍藏着书香、翰墨香,另一端弥漫着晨钟声、香火味,两端相济,而读书声与念经声又声情并茂。这或是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辞别先贤杨守敬,我在敬岛上漫步,有一只渔船从清江荡漾到我的目光里。渔民摇着木浆,也把自己、渔船与清江水摇成一幅水墨画,气韵十分生动。
夜下,我入住天龙湾一家旅馆。这家旅馆通人心,尚人性。我站在窗前,看夜下的天龙湾,一切静极了,静得让我心动,独能听见空气清新的流动声。这是一个令人降压、脱俗与静心的家园。
有时候,静,不是形容词,是一种卓尔不群的格调,更是一种引人入胜的品质。置身于静静的天龙湾,我也靠近了“见素抱朴”、“离境坐忘”的境界。
水乡
梦境不一定是虚构的,也不一定是幻觉。久居都市,我的梦境大多在高分贝的噪音中支离了。都市也有森林,但那是由高楼、广厦合成的。钢筋混凝土长不出梦境,即便长出了梦境,也说不上美妙。前不久,我到“梦里水乡”一游,恍若进入了深深的梦境,寻找到了一种与日常生活完全不同的感觉。
梦里水乡,名符其实。长江之北、汉水之南的江汉平原上,嵌着一颗明珠:仙桃。仙桃有仙境,梦里水乡便是典例。
梦里水乡有一座荷塘村,傍水而居,青砖,黛瓦,镂花木窗,跌宕的马头墙,檐角飞翘却不张扬。而以竹、草、土、芦苇为元素构成的农家小屋,闲适而恬静,不事雕琢,情绪温和。尤其是每户人家高挂在屋檐下的马灯,用叙事的姿态,回忆着这片土地过往的岁月。荷塘村天时、地利、人和咸备,向吉,尚祥,正应了“流水门前过,绿树村边合”的意境。时值谷雨节气,我穿行于荷塘村,虽见不着东晋岚气飘绕的南山,也因时令,没有遍地的菊花让我采摘,但我悠然地通往了陶渊明清淡、脱尘的状态。荷塘村质朴,淡定,面拙而骨子里藏巧,雅趣深致,一点也不俗气,而且,村小却有大格局。
坐一艘小木船,我渐入遍水的梦境。绛云在霄,舒卷自如。从船窗里将目光放牧到远天,我惊奇地发现,我的目光十分流畅地进入到了白云之间,随白云一起逍遥,并与白云同乐。我曾把目光伸向都市的远天,渴望目光与白云相遇,但目光往往是被入云的建筑反弹回来。
我以为,梦里水乡临摹了唐诗宋词的神韵。我还以为,梦里水乡的神韵之源头是楚辞。梦里水乡没有粉黛,也没有娇喘,更没有媚骨,不轻佻,不潦草,一切呈自然、平和与清丽之貌。
梦里水乡以水为脉,而这方水有涵养,有境界,悦人不说,独说怡物。温柔的水域里,养着大片的池杉。池杉主干挺直,树冠尖塔形,高及二十五米。据说,这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种植的。池杉树干基部膨大,呼吸根呈曲膝状。所以,这方水域的水位是常设的。放眼望去,这片池杉横成行,纵也成行,一点不缭乱。论其规模,名列全国池杉之首。说它是一座天然的大氧吧,不是虚言。行走于池杉丛林之中,我禁不住做深呼吸,清除肺叶里的垃圾,引入新鲜的氧气。
鸟声是上帝赐给人类的音乐与福音。池杉之间,有鸟鸣唤醒了我的乡愁。小天鹅涉水优雅,发现螺、蠕虫、小鱼和植物种子后,便会饱食一顿美味。白鹭衔着王维、杜甫的诗句,从唐朝起飞,飞到了梦里水乡;白鹭也衔着陆游、寇准的诗情,自宋朝起飞,飞到了梦里水乡。水乡风晨月夕,空气湿润,宜于人入梦,也宜于鸟入梦。
临水,散布着绿竹、丁香、牡丹、桂花、玉兰、梅花、茶花、石榴、桃花、八仙、紫薇、玫瑰诸岛,十二类植物也在这方水土出泥而入梦。正是因为有了梦,它们才应着时令拔节生长,循季绽放,以各自的姿容独居一格,讲述着植物与大地与节气的血脉关联,不会让梦里水乡在任何季节里孤单与寂寞。昼餐水乡之灵气,夜饮仙桃之精华,这些植物次第浮动着暗香,也忠诚传播着人文的延续。在我看来,它们生来就不是应景的,是缀在宇宙之间的万物生命链。
水边还泊着另外一种风景,这就是与十二花岛相呼应的十二仙女。仙女坐在近岸的木船上,怀抱一把半梨形的琵琶,左手按弦,右指弹奏,以简朴的旋律向水乡抒情,也以细腻的格调向我倾诉。于是,仙女的纤纤玉手拨动了中国历史,琵琶之声雄伟奇特,于遥远的《十面埋伏》之中,披着垓下的战尘,敲击着我的耳膜。不过,水乡早已洗去了楚汉的战尘、项羽的血迹和虞姬的香艳,仙女的五指与琵琶的四弦相交之际,是止戈息甲,天下太平。于是,乐曲也舒展、优美起来,回澜拍岸之后,便是风回曲水、水深云际、花影层叠。
泊船上,也泊着另外一种仙女。仙女长袖玉立,安静文秀,怀抱里虽没琵琶,却含着水乡的梦境,温婉而不哀婉。隔着一段水路,我的目光踏水而去,只见仙女目光清澈,璞玉浑金,眉宇间全是回归自然的表情。我没有惊艳的感觉,胸中也没有埋伏一朵裙钗,却有沉静的心态。仙女本分地站在木船上,如唐末的一首小诗,又如五代的一首小词,但不可忽视,也不可忽略。
一曲《渔舟唱晚》牵走了我的视听。走过去,我看见一位仙女弹着古筝,舒缓而饱满的曲调在十二根弦上如水荡漾,更有碧波、渔船在纤尘不染的曲调中起伏。这位弹古筝的仙女发髻高耸,高雅脱俗,把《滕王阁序》的韵味表达得很悠然,也很斑斓,虽没有“响穷彭蠡之滨”的气势,却有王勃笔下“渔舟唱晚”的意象。静听这首古筝名曲,我看到了初唐的晚霞、随波的渔船与载歌的渔民。
亲水平台上,另有三四名仙女舞姿优雅,注释着古筝名曲。她们长裙曳地,头上还摇动着一把油纸伞,走着含羞的细步,却也落落大方,一点也没有取悦于人的妖态。
有时候,我还听见了沔阳花鼓戏的唱腔。仙桃原名沔阳,百里沃野上,河渠网织。正是河水的浸濡,唱腔优美、明亮。据说,仙桃人有一美谚:“听了花鼓戏哟喂哟,害病不吃药。”于是,我多听了几段花鼓戏,也在池杉丛林中“哟喂哟”了几嗓,想从梦里水乡带回健康。
梦里水乡有河声、船声、琴声,也有鸟翔、牛耕、树影,但我的视听系统却十分宁静,因为这是一个可以洗涤灵魂的地方。
但愿我是一株池杉,种植在梦里水乡里。
(作者系湖北省长江文化研究院副院长兼总编辑、《中华长江文化大系》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