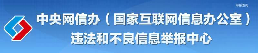在国人的记忆里,过年总藏着最绵长的温情,依着传统习俗,这趟欢喜的旅程大抵从腊月二十四启幕,至正月十五元宵落帷。于走过岁岁年年的成年人而言,这近二十天的光景,看似是偷得浮生的休闲,实则满是烟火人间的忙碌,藏着鄂东大地独有的年俗韵味。
鄂东的年,是从腊月二十四的小年开始的。这一日也被称作 “孩子年”“伢儿年”,若是偏远山区遇着大雪封山,年味便会更早漫开,腊月二十左右,就有了小年的前奏。想来这小年的由来,总与旧时的农耕生活分不开。彼时生产力低下,日子过得俭朴,一年到头,唯有丰收之时能好好庆贺一番。杀猪宰羊备年货的忙碌里,人们总先想着给孩子们一份特殊的优待,让这份年的甜,先甜了孩童的时光。
小年过后,年味愈浓,腊月二十八,便是鄂东独有的 “岳母节”。姑娘领着姑爷回娘家辞年,提上精心准备的年货,话着家常,把孝心与惦念揉进年的光景里。待年的脚步走到大年三十,才是真正的过年时刻。这一日的时光被安排得满满当当,上午是节前最后的细致检查,将家里的角角落落收拾妥帖;午后便要去往祖坟山,摆上供品祭祀先人,在袅袅烟火里,念着血脉的传承,诉着新年的祈愿。归来后,贴春联是必不可少的仪式,红底黑字的春联一贴,年的喜庆便撞进眼里。而后放长鞭辞年,噼啪的鞭炮声里,一家人围坐桌前,吃一顿热气腾腾的年夜团圆饭。守着春晚,聊着过往,守岁至凌晨零点,春雷与炮仗齐鸣,声声都在迎接新岁的到来。
新年的日子,藏着走亲访友的温情。大年初一,给父母拜年,道一声新年安康,承一份亲情的暖;初二往岳父岳母家去,把新春的祝福送到;初三至初八,串街巷、访亲友,彼此道贺,共享年的欢喜。这份热闹,一直延续到正月十五,元宵的花灯亮起,汤圆甜糯入喉,过年的这场盛宴便告一段落。烟火人间重归寻常,生活又回到从容的正轨,只把年的美好,藏进心底。
年年岁岁年相似,岁岁年年感不同。人生的境遇辗转,让不同年岁的我们,揣着不一样的过年心境。儿时的年,是藏在心底的期盼,日日盼,夜夜念。盼着有香甜的吃食,有崭新的衣裳,有新奇的玩物,更盼着长辈递来的红包,那点点压岁钱,是童年最珍贵的欢喜。可随着年岁渐长,那份对年的热切,却慢慢淡了。仿佛过年不过是吃穿玩赏,不过是迎来送往,少了儿时的雀跃。想来大抵是,日子清贫时,过年是一年到头的念想,是对美好日子的期盼;而今生活顺遂,日日皆有甜,日日都似年,反倒让真正的新年,少了几分别样的兴致。
年,最初不过是一个简单的时间量词,在时空的流转里,帮我们丈量岁月,把握人生四季;过年,也只是农耕文化里的历法实用,是农人顺应节气、契合农时的安排。只是时光流转,岁月沉淀,它慢慢褪去了最初的实用底色,演变成一场庆贺丰收的文化盛典,成了刻在国人骨子里的仪式,藏着一个民族的情感与传承。
回望年节,心中总感慨万端。年,本是多面的模样,若只盯着吃喝穿戴,那它不过是一场物欲的盛宴,一个流于表面的物质之年;若只执着于文化娱乐,那它也只是一场精神的狂欢,一个止于热闹的文化之年。倘若单从一个角度去解读年,便如同曲解了那传说中的年兽,它本是在特殊的日子里,想走进人间与我们共享欢喜,却因片面的解读,被误读,被驱赶,失了原本的模样。
细细品味,年与过年,是中华民族沿袭了数千年的文化习俗,早已像民族特有的基因,深深融入我们的血脉,刻进每个国人的骨血里。每至雪花飘飞、寒冬岁末,这份刻在骨子里的情愫,便如荷尔蒙般在心底躁动,让无数游子放下手头的忙碌,生出归乡的执念。在人生匆匆的步履中,年就像一记温柔的刹车,让我们停下奔波的脚步,回望故土,惦念家园,而后踏着归程,奔赴那一方熟悉的烟火。
我总爱这般联想,年于我们每个人而言,何尝不是一个伴随一生的小号?在岁月的长风里,它会定时在耳畔响起,那悠长婉转的号声,轻轻诉说着生命的时辰,提醒着我们时光的流转。在花谢花开、冬去春回的四季更迭里,它吹灭旧岁的最后一丝遗憾与怅惘,吹亮新年的第一缕希望与晨曦。
这小号的旋律,有时如母亲唤儿,温柔又深情,轻轻呼唤着我们放慢人生的急进步履,带着一身风尘,踏上归乡的旅程,在亲情的港湾里疗愈疲惫;有时又如父亲的嘱托,高亢又激昂,催着我们迎着乍暖还寒的春风,放下过往的眷恋,为了更美好的生活,踏上全新的人生征程。
年,终究是那支藏在心底的小号,是岁月之神赠予我们的随身法宝。我们对它,总是怀着几分期待,又藏着几分怯意。期待着它的响起,能让我们与亲友相聚,能让我们迎来新的希望;也怯于它的响起,感叹时光飞逝,感慨岁月匆匆。可这悠长的号角,终究会荡人心脾,撼人灵魂;这深深的号鸣,总会让我们在车马匆匆的疲惫里,回望家园与母亲,回归季节与起点。在熙攘的现代都市里,循着这号声,回望来时的路,寻回那份自然的人性,安放那颗漂泊的心灵。
作者:湖北黄冈应急管理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陈红
责编:万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