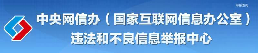宋末元初,王英镇谷贞村地瘠,石多土少,泉味涩而田禾槁。庄稼年年歉收,人穷得叮当响,病也跟着来——今儿个拉肚子,明儿个生烂疮。村里人叹气:“这鬼地方,连麻雀都不肯多停一会儿。”

就在这样的苦日子里,出了个姑娘,叫青禾。她阿爹是土郎中,家里挂满了干草药。阿爹常说:“药再好,也得有好水煎。”青禾把这句话记在心里。谁头疼脑热,她拔腿就去摘草药;谁家孩子夜里哭,她熬好了药汤一勺一勺喂。可草药只能缓一缓,没有干净水,病还是断不了根。“要是能有一泉清水就好了。”青禾常常蹲在干裂的田埂上这么想。
村口的老槐树底下,常坐着一位白胡子老爷爷,摇着蒲扇讲故事。他说:“后山深处有块镜澜石,通体透蓝,像月亮沉在水底。石头旁守着一条红鲤鱼,是湖里的小神仙。心术不正的人,走不到跟前;心地干净的人,石头就给他一汪好水。”孩子们听得直咽口水,可谁也没敢真去找。山高林密,瘴雾重重,进去的人十有八九回不来。青禾却暗暗上了心。
第二天鸡还没叫,青禾就背起竹篓,揣了两个红薯、一把镰刀,悄悄出了门。山路难走,先是碎石扎脚,后是荆棘扯衣。她割一捆野藤当绳子,一步一步挪。渴了,就喝石缝里的滴水;饿了,就啃生红薯。天蒙蒙亮,她攀上一道石梁,眼前忽然一亮:一湾碧潭静静躺在谷底,潭中央,一块蓝莹莹的大石头正泛着柔光。石头旁,一条红鲤鱼摆着尾,鳞片像晚霞一样。
青禾跪在石头前,把村里人喝黄泥水、庄稼枯死、孩子生病的事一句一句说了。说到伤心处,眼泪吧嗒吧嗒落在石头上。说来也奇,泪珠一沾石面,石头竟“嗡”地一声,荡出一圈圈蓝光。红鲤鱼打了个转,忽然“噗”地跃出水面,在半空里一摇身,竟变成一个穿红袍的少年,眉心一点银鳞。“我叫镜澜。”少年声音清亮,“千百年来,无数人找我讨水,只为发财、为争地,没一个像你一样哭别人苦。”
他抬手一指,石底“咕噜咕噜”冒银泉,像煮沸的月光。“带回去吧,但记住——水养人,人也得养水,贪心一起,泉就断。”
青禾用竹筒接满第一捧水,双手捧着往回走。说来也怪,一路只要她经过,干裂的土就润出一道湿痕,像给她指路。
回到村里,她把水倒进泉中,只听“咚”一声,泉水像开了锅,清凌凌的水一路漫上来。不到半天,泉水溢出,顺着田沟哗啦啦跑,焦黄的稻苗转眼挺直了腰。
村里人奔走相告:“青禾讨回神水了!”大家按她教的办法,挖渠的挖渠,筑堤的筑堤,不出一个月,泉水所经之处都亮堂堂的。泉水清得能照见天上的云朵,大家给它起名——“永清泉”。

好景不长。山那头的黑风怪闻到水汽,腾起漫天黄沙,怪叫着要堵泉眼。那天傍晚,天忽然暗得像扣了锅,飞沙走石打在人脸上生疼。泉水被吹得掀起黑浪,眼看就要把新开的渠口埋了。青禾冲在最前头,用身子扑在泉眼上,两臂死死箍住石沿。沙石噼里啪啦砸在她背上,血顺着脖子往下流。
就在这当口,湖面“哗啦”一声巨响,镜澜化作一条几丈长的火红大鲤鱼,鳞片像烧红的铁,尾巴一甩,把沙浪劈成两半。一人一鱼,跟黑风怪斗了足足一夜。鸡叫三遍时,黑风怪一声哀嚎,卷着残沙逃回山缝。青禾却再也撑不住,身子一软,倒进水里,泉水立刻染出一圈淡淡的红。
镜澜抱着她,眼眶也红了。“说好水养人、人养水,你倒把命都搭进来了。”他轻轻把青禾放进泉心最深最清的地方,双手合十,念起古老咒语。
只见泉水中慢慢升起一缕银光,像温柔的月光,又像青禾常对病人露出的笑。银光融进泉水,再也分不开。从那以后,谷贞的水一年四季不枯不溢,冬天冒热气,夏天沁心凉。
清晨,水面铺一层淡粉霞光,老人说那是青禾在笑;月夜,水波闪着细碎银鳞,孩子们说那是镜澜在打手电巡泉。
而那条红鲤鱼,再也没人见过。有人路过清水泉,偶尔能听见“咕噜”一声水响,像是谁在提醒:“喝水别忘了挖井人。”
王英镇谷贞村一年比一年富,每当外地的游客经过时,村里老人就会慢悠悠地讲这段老话儿,末了总补一句:“记住,这泉水是拿命换来的,咱得替好人守好它。”
风从泉水吹过,芦苇沙沙响,好像青禾在轻轻答应。
(整理:方书坦)
责任编辑:万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