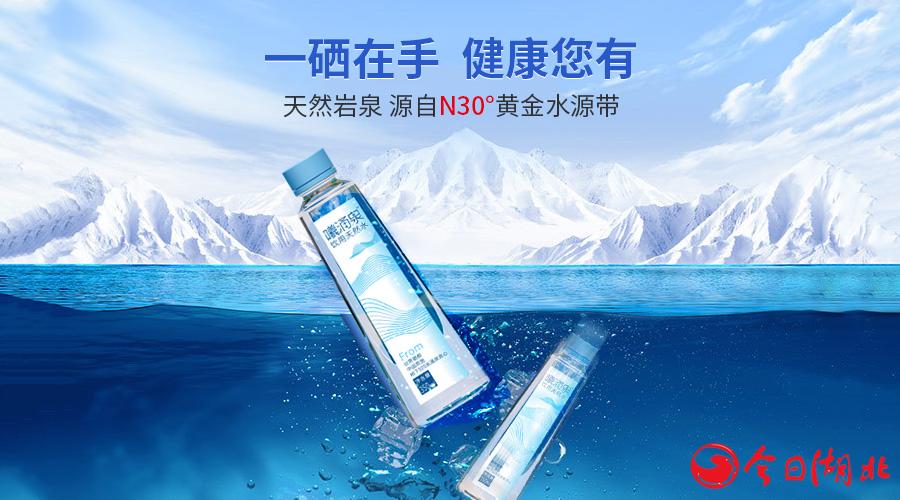《新加坡调解公约》对我国商事调解与商事仲裁
协同发展的影响
宫步坦、刘文昭
摘要:已于2020年9月12日生效的《新加坡调解公约》是国际商事纠纷解决制度的一项重大变革,是国际商事调解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新加坡调解公约》填补了通过调解方式解决国际商事纠纷的和解协议无法在相关国家或地区予以执行的空白。《新加坡调解公约》与《纽约公约》《选择法院协议公约》共同构建起了调解、仲裁、审判三足鼎立的国际民商事争议解决及执行框架。《新加坡调解公约》的出台及生效,在给我国商事调解发展带来机遇与挑战的同时,也会对我国处理商事调解与其他解纷机制的关系,包括商事调解与商事仲裁的协同发展关系,产生深远影响。
关键词:《新加坡调解公约》 商事调解 商事仲裁 协同发展
《联合国关于调解所产生的国际和解协议公约》(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Agreements Resulting from Mediation,简称《新加坡调解公约》),2018年6月26日由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正式批准,2018年12月20日在第73届联合国大会上通过。2019年8月7日,该公约在新加坡开放供各国签署,包括中国在内的46个国家成为首批签署国。截至2020年7月31日,共有53个国家签署了公约,5个国家批准了公约。根据公约第14条规定,该公约于第三个国家批准后的6个月后生效。卡塔尔作为继新加坡与斐济之后第三个批准国,于2020年3月12日正式批准;该公约已于2020年9月12日起生效。
《新加坡调解公约》旨在解决国际商事调解达成的和解协议的跨境执行问题,赋予调解所产生的国际商事和解协议强制执行力,促进国际商事和解协议的跨境流动。该公约填补了国际商事调解解纷机制在执行领域的空白,势必对国际商事调解,尤其是签署国的国际商事调解乃至商事调解产生重要影响,同时也会影响到商事调解与其他解纷机制的协同发展关系。
我国作为《新加坡调解公约》的首批签署国,紧跟国际商事调解发展的趋势能为我国商事调解发展带来契机,同时也会给我国尚不成熟的商事调解制度带来很大的冲击。在营商环境法治化背景下,根据商事纠纷的特征重构我国商事调解制度,健全和完善商事纠纷解决机制,十分重要。从国际层面看,《新加坡调解公约》为当事人达成的国际商事和解协议的跨境执行,提供了统一有效的框架,必将大大推动以调解方式解决国际商事纠纷。从国内层面看,特定政策背景下确立的中国商事调解制度雏形,必将迅速改写商事调解机构与商事审判机构、商事仲裁机构之间的格局关系和发展模式。概言之,《新加坡调解公约》带来的契机与冲击,并不仅局限于商事调解领域本身,也会延伸至商事调解与其他解纷机制,尤其是商事调解与商事仲裁的协同发展。
一、《新加坡调解公约》对我国商事调解发展的影响
调解是中国在其数千年的漫长过程中逐渐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种解决社会矛盾和冲突的重要方式。调解虽产生并植根于我国辽阔地域,但我国商事调解发展却远远落后于国际上商事调解的发展。这主要源于,长期以来,普遍认为商事调解从分类上应当属于人民调解的范畴。商事调解受以人民调解为基础的“大调解”政策影响巨大,导致我国商事调解的生存空间被一再压缩。主要的精力都集中在了人民调解制度的建设上,对更具专业性的调解机构的商事调解、仲裁机构的商事调解并没有投入更多的精力。在最高人民法院政策文件的传统语境中,“大调解”格局由人民调解、行政调解与司法调解组成,直至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建立健全诉讼和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2009年最高院若干意见》,提及“完善诉讼与仲裁、行政调处、人民调解、商事调解、行业调解以及其他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之间的衔接机制”,才首次将商事调解从人民调解中剥离出来,单独作为与诉讼、仲裁、人民调解等相并列、相平行的纠纷解决方式。至今虽已历经十余年发展,但由于我国并没有独立的《调解法》或《商事调解法》,也未形成一套完整的商事调解制度,对商事调解的定位模糊、认识不足,导致我国商事调解发展进程缓慢。
(一)对我国解决国际商事纠纷理念的影响
诉讼、仲裁、调解是解决商事争议的三大途径,执行相关判决、裁决、和解协议是定分止争的终极。法院判决因涉及到法域之间的司法主权,跨境执行难度大,一直以来并不被国际商事争议当事人所青睐。在20世纪中期以前,国际商事争议当事人更加倾向于通过调解解决争议;20世纪中期之后,仲裁才逐渐取代调解成为更受当事人偏好的争议解决方式。出现此种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1958年《纽约公约》赋予了国际商事仲裁裁决强制执行力,使得仲裁裁决能在各缔约国之间得到承认与执行。调解所产生的和解协议性质上仅仅属于合同契约,缺乏强制执行力,这成为使用调解解决商事争议的最大障碍。据此可知,国际商事争议当事人选择何种争议解决方式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解纷结果是否具有强制执行力。《新加坡调解公约》的诞生是对调解越来越多地在国内和国际商务实践中得到运用的有效回应,是商事纠纷当事人调解需求在国际社会的集大成体现。
《新加坡调解公约》赋予和解协议强制执行力,折射出国际社会对当事人高度意思自治的普遍认可。与《纽约公约》相较,《新加坡调解公约》不再使用“承认”(recognition)的提法,开创性地规定了“直接执行机制”,略过对和解协议的承认,直入执行程序,凸显了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高度认可。
《新加坡调解公约》对我国解决国际商事纠纷理念产生的影响,一个重要体现是加强商事调解在涉“一带一路”国际商事纠纷中的适用。2015年6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人民法院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若干意见》(简称《2015年意见》),提出“支持中外当事人通过调解、仲裁等非诉讼方式解决纠纷。要进一步推动完善商事调解、仲裁调解、人民调解、行政调解、行业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工作体系”。2018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建议“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和机构的意见》(简称《2018年两办意见》),提出支持“一带一路”国际商事纠纷通过调解、仲裁等方式解决;对当事人之间的跨境商事纠纷,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根据当事人自愿原则先行调解;支持具备条件、在国际上享有良好声誉的国内调解机构开展涉“一带一路”国际商事调解。2018年11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确定首批纳入“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国际商事仲裁及调解机构,将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调解中心、上海经贸商事调解中心作为首批纳入该机制的调解机构。2019年12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进一步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简称《2019年意见》提出“大力支持国际仲裁、调解发展,完善新型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拓展国际商事法庭‘一站式’纠纷解决平台的国际商事仲裁机构、国际商事调解机构名单”、“在国际商事案件中贯彻调解优先原则,当事人同意的,可在任何阶段共同选择国际商事专家委员,国际商事调解机构或国际商事法庭进行调解”、“积极发挥侨联、行业协会、商会等民间组织和机构力量,支持建立国际商事纠纷联合调解机制,促进纠纷的简便平和解决”。
从最高人民法院在我国签署《新加坡调解公约》后发布的《2019年意见》与之前的《2015年意见》《2018年两办意见》对比,可一窥在签署前后我国解决国际商事纠纷理念的变化。第一,《2015年意见》和《2018年两办意见》都是支持调解,《2019年意见》则变成了“大力”支持调解,加重了对调解的支持力度;第二,《2018年两办意见》提出国内调解机构开展涉“一带一路”国际商事调解,《2019年意见》则拓展“国际商事调解机构”名单,通过推动和发展专业商事调解组织,国际商事调解进入实操层面;第三,《2018年两办意见》提出的是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根据当事人自愿原则先行调解,即在启动诉讼或仲裁程序前,当事人有权利申请由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先组织调解,《2019年意见》则首次提出“在国际商事案件中贯彻调解优先原则”,并且当事人可随时进行调解,也可以根据自身意愿选择国际商事专家委员、国际商事调解机构或国际商事法庭进行调解,而不仅局限于由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先行调解,充分尊重当事人调解的意思自治。
《新加坡调解公约》对我国解决国际商事纠纷理念已初露端倪。叶落知秋,《新加坡调解公约》所折射出来的对当事人意思自治高度认可的理念,势必也会促使今后我国在解决解决国际商事纠纷更加趋同于这一理念。推而广之,更将契约精神、商法自治、社会自治等商事理念推向整个中国社会。理念外化于形,进而推动我国重新定位商事调解制度。
(二)对我国商事调解定位的影响
《2009年最高院若干意见》首次出现了“商事调解”的身影,并将商事调解也列为大调解的一种,与人民调解、法院调解、行政调解并列。但一直以来,我国关于调解的规定分布在各部门法和司法解释中。2010年虽出台了《人民调解法》,但《人民调解法》并未规定商事调解。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全国工商联印发了《关于发挥商会调解优势推进民营经济领域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的意见》,提到具备条件的商会可以成立专业的商事调解组织。但至今仍然缺乏系统的调解法律,也并无商事调解统一立法。实践中商事调解参照的法律主要是《人民调解法》。这也导致商事调解普遍被认为属于人民调解的范畴,模糊了商事调解与人民调解的界限,掩盖了商事调解本身的特性,最终导致对商事调解的定位模糊不清。借助于《新加坡调解公约》的出台,有助于厘清商事调解的地位。
《新加坡调解公约》是商事调解发展历史上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文件,被法律界人士誉为调解领域的《纽约公约》,更有评论将其与国际商事仲裁领域的《纽约公约》以及国际商事诉讼领域的《承认与执行外国民商事判决公约》一起称为国际民商事承认与执行领域的“三驾马车”。在此之前,诉讼、仲裁、调解虽然被视为解决国际商事纠纷的三大途径,但调解所达成的和解协议缺乏强制执行力,使得调解的功效大打折扣,调解的地位略低一筹。在《新加坡调解公约》将国际商事调解提升至与国际商事仲裁、国际商事诉讼同一高度的国际大背景下,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商事调解在商事解纷机制中的独立性地位。
但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大调解”格局的影响,商事调解独立性地位的塑造并非一蹴而就,应是循序渐进的发展过程。主要可从以下两方面重新定位商事调解:(1)从调解向内自省而言,商事调解必须占据独立的一席之地,不应作为某一类别调解如人民调解、行业调解等的子调解类别。如将调解看作一个夹心水果蛋糕,商事调解应是从整个蛋糕切出来的一块,非为某一块里面的水果夹心存在。(2)从调解对外延伸而言,商事调解应作为与商事诉讼、商事仲裁相并行的独立的解纷机制,非为商事诉讼或商事仲裁附属的程序性工具。
值得注意的是,通过对比上文提及的三个意见可知,《2015年意见》强调了完善商事调解与其他形式调解的联动工作体系,《2018年两办意见》强调了积极培育并完善诉讼、仲裁、调解有机衔接的争端解决服务保障机制,推动建立诉讼与调解、仲裁有效衔接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2019年意见》则对上述两点均未予提及,更加强调的是“在国际商事案件中贯彻调解优先原则”,建立“商事纠纷联合调解机制”,弱化了商事调解和其他调解的关联性,以及商事调解和商事诉讼、商事仲裁的关联性,突出了商事调解的独立性与自成体系性。
二、《新加坡调解公约》对我国当前商事调解与商事仲裁协同发展模式的影响
当前,我国商事调解与商事仲裁协同发展,主要表现为由仲裁机构对和解协议的效力予以确认的确认仲裁模式和仲裁中调解(Arb-Med)的仲调结合模式。鉴于《新加坡调解公约》是针对国际商事调解所产生和解协议的执行,在当前我国商事调解法律体系及制度框架未有大变动的情况下,《新加坡调解公约》对我国商事调解与商事仲裁结合的影响将主要体现在国际(涉外)商事调解与商事仲裁方面,对国内(非涉外)商事调解与商事仲裁的影响则会有不同的可能性:一是《新加坡调解公约》先作用于国际(涉外)商事调解与商事仲裁,通过此种作用倒逼国内(非涉外)商事调解与商事仲裁与国际发展接轨,形成内外一致的单轨制发展体制;二是分化国际(涉外)商事调解与商事仲裁、与国内(非涉外)商事调解与商事仲裁的发展路径,形成内外有别的双轨制发展体制。在不确定性影响下,本部分将主要从国际(涉外)商事领域论述《新加坡调解公约》对确认仲裁及仲裁中调解模式的影响。
(一)我国当前商事调解与商事仲裁协同发展的主要模式
在当前的商事调解体系中,因调解产生的和解协议仅具有民事合同性质,履行和解协议要么基于当事人“头顶上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准则”,要么依赖于仲裁机构的仲裁确认或法院的司法确认赋予其强制执行力,或者更甚者,在以调解解决此纠纷后,当事双方因履行和解协议发生争议后再将因调解产生的和解协议作为彼纠纷诉诸法院或仲裁机构。此情形下,商事调解与商事仲裁结合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当事人合意由仲裁机构对和解协议的效力予以确认,即确认仲裁,与司法确认具有殊途同归之感。此外,仲裁中调解(Arb-Med)模式历经六十年的发展,也成为我国商事调解与商事仲裁协同发展的一个典型模式。
1.确认仲裁模式
确认仲裁,首创于武汉仲裁委员会。武汉仲裁委员会从1998年开始涉足确认仲裁;2007年,确认仲裁正式进入《武汉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确认仲裁,是指仲裁庭根据当事人的请求和仲裁规则,对当事人之间签订的合同或就解决争议达成的和解协议进行审理,依法对合同或和解协议的效力予以裁决的仲裁行为。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一条明确了“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并由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的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性质”,同样,商事和解协议亦具有合同性质。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人民法院进一步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2016年最高院若干意见》),提出“经行政机关、人民调解组织、商事调解组织、行业调解组织或者其他具有调解职能的组织调解达成的具有民事合同性质的协议,当事人可以向调解组织所在地基层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法庭依法申请确认其效力”,则是最高人民法院第一次明确规定人民调解协议之外的其他调解协议也能够适用司法确认程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十九条第二款之规定“仲裁庭有权确认合同的效力”,由仲裁庭对具有合同性质的和解协议效力予以裁决,将和解协议转化为具有强制执行力的仲裁裁决,以此弥补和解协议缺乏强制执行力的短板。
2.仲裁中调解模式
“仲裁中调解”(Arb-Med),即通常所说的仲调结合,是指在仲裁程序进行过程中,由仲裁员对案件进行调解,调解不成后或调解成功后再恢复进行仲裁程序。该做法在中国最早源于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仲裁实践。1994年颁布的《仲裁法》第五十一条规定“仲裁庭在作出裁决前,可以先行调解。当事人自愿调解的,仲裁庭应当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作出裁决。 调解达成协议的,仲裁庭应当制作调解书或者根据协议的结果制作裁决书。调解书与裁决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1995年7月28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仲裁委员会仲裁暂行规则示范文本》将该条内容写入其中;各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基本上都采纳了该条:作为践行“仲裁中调解”的法律依据。经近六十年的发展,仲裁中调解模式在解决纠纷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从下表数据可窥一斑。
2014-2019年以调解和解方式结案的案件数量
年度 | 仲裁委员会数量 | 仲裁案件数 | 调解和解方式结案 | 调解和解方式结案占比 |
2014 | 235 | 113660 | 74200 | 65% |
2015 | 244 | 136924 | 56659 | 41% |
2016 | 251 | 208545 | 121717 | 58% |
2017 | 251 | 239360 | 69450 | 29% |
2018 | 255 | 544536 | 140281 | 26% |
2019 | 253 | 486955 | 85980 | 18% |
(二)《新加坡调解公约》对确认仲裁模式的影响
在《新加坡调解公约》赋予了国际商事和解协议强制执行力的情况下,国际和解协议的强制执行与否将不再依赖于法院或仲裁机构对于和解协议效力的确认,而是在公约国之间可直接依据《新加坡调解公约》申请执行。那么在国际商事领域,确认仲裁的生存空间将会受到挤压。在《新加坡调解公约》目前远未达到《纽约公约》如此高参与度的情况下,该种影响可能会被质疑,因为在非《新加坡调解公约》公约国之间,还是需要将和解协议转化为在《纽约公约》项下具有可执行性的仲裁裁决。但仲裁庭根据当事人在提起仲裁前已达成的和解协议做出的“仲裁裁决”并不足以构成美国法院承认与执行的仲裁裁决。此对仲裁确认提出了新的挑战与困境。在《新加坡调解公约》的影响下,促使我们重新审视在国际商事调解与商事仲裁中确认仲裁的作用。
(三)《新加坡调解公约》对仲裁中调解模式的影响
仲裁中调解模式下,仲裁庭调解成功后有两种结案方式:(1)仲裁庭制作调解书;(2)仲裁庭根据调解协议的结果制作裁决书。那么调解书与裁决书是否具有同等效力呢?从可否直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而言,因调解书或裁决书皆由仲裁庭作出,《仲裁法》第五十一条规定“调解达成协议的,仲裁庭应当制作调解书或者根据协议的结果制作裁决书。调解书与裁决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根据《仲裁法》第六章和《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六章,由仲裁庭制作的调解书与裁决书可以作为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依据。但从能否根据《纽约公约》申请承认与执行而言,调解书与裁决书并不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因《纽约公约》的调整范围是仲裁协议和仲裁裁决书,故该类调解书不能向《纽约公约》缔约国申请强制执行。
那么该类调解书在不适用《纽约公约》的情况下,能否适用《新加坡调解公约》在公约国得到执行呢?《新加坡调解公约》第1条第3款规定“本公约不适用于:(a)以下和解协议:(一)经由法院批准或者系在法院相关程度过程中订立的协议;和(二)可在该法院所在国作为判决执行的协议;(b)已记录在案并可作为仲裁裁决执行的协议”,主要在于如何理解(b)款所述的“可作为仲裁裁决执行的协议”是指该协议能在国内可作为仲裁裁决执行还是指依照《纽约公约》可作为仲裁裁决执行?如果是前者,那么该调解书将不能适用《新加坡调解公约》在缔约国申请执行,如果是后者,在该类调解书不能依据《纽约公约》作为仲裁裁决执行的情况下,该类调解书即可被纳入《新加坡调解公约》的适用范围。
国内学术界普遍认为《新加坡调解公约》第1条第3款将经法院与仲裁机构调解形成的和解协议明确排除在适用范围外。因此,仲裁庭制作的调解书并不适用《新加坡调解公约》。在仲裁庭制作的调解书既无法适用《纽约公约》作为仲裁裁决在缔约国申请承认与执行,也无法适用《新加坡调解公约》作为和解协议在缔约国申请执行的困境下,那么势必对仲裁庭制作调解书结案方式造成冲击,进而对仲裁中调解的仲调结合模式产生一定的冲击,尤其是在国际商事仲裁案件中。
三、借助《新加坡调解公约》推动我国商事调解与商事仲裁协同发展的几点思考
首先,转变理念,重新定位商事调解,重新审视商事调解与商事仲裁的关系。一直以来,我国商事调解并不具有独立的地位,加之因调解达成的和解协议需要依赖仲裁予以确认,才能赋予其强制执行力,造成了商事调解在与商事仲裁的关系中更多地体现了一种从属性。无论是确认仲裁模式还是仲裁中调解模式,商事调解都仅仅只是解纷的手段,而非为一种具有独立性的解纷机制。《新加坡调解公约》映射出解决国际商事纠纷理念的变化,在国际商事调解领域更加注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促使我们重新审视商事调解的地位,重新审视商事调解与商事仲裁的关系。笔者认为,协同发展的探索应以商事调解作为独立的解纷机制为前提,将商事调解与商事仲裁视作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的两个解纷机制。在尊重两者独立性的基础上,分析厘清两者的共同性与差异性,找到最佳的协同点,通过高效可行的协同机制,促使两种纠纷机制发挥最大效能。
其次,以当下内外有别、长远内外一致的基点探索协同发展机制。《新加坡调解公约》对我国当前商事调解与商事仲裁协同发展的模式会造成一定冲击,此种冲击更多地体现在国际商事方面。因此,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无论未来国际与国内是并行的单轨制还是分扬的双轨制,在当下探索协同机制时,必须注重内外有别的差异化。然从长远发展的角度而言,我们应全面整体地探索商事调解与商事仲裁协同发展的新路径,注重内外一致协同发展机制的研究与探索。
再次,根据《新加坡调解公约》与《纽约公约》的差异性与对接路径,注重商事调解与商事仲裁协同争议解决方案的高效设计。在这两个公约的公约国并非完全重合的情况下,哪些情况下适合调解、哪些情况下适合仲裁,将是一门高深的学问。此要求在国际商事调解与商事仲裁实践当中,包括调解组织及调解员、仲裁机构及仲裁员等在内的参与争议解决的各方主体,甚至前期把控法律风险的主体包括律师、法务等,对两个公约的内容及适用应具有精深的了解与认知;这样才能通过合理高效的争议解决方案设计,最大限度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以使调解与仲裁切实为国际商事主体开展国际商事活动保驾护航。
最后,注意商事调解与机构仲裁、商事调解与临时仲裁的差异化协同机制探索。另一个虽受《新加坡调解公约》影响不大,但在探索商事调解与商事仲裁协同发展时所不可忽略的内容,是应注意区分商事调解与机构仲裁、商事调解与临时仲裁的差异化协同发展机制。从世界范围看,临时仲裁是国际上普遍使用的一种民商事争议解决手段,它与机构仲裁相辅相成,相互融合,在纠纷的解决中各自发挥着作用。因此,在国际上,对临时仲裁与机构仲裁同等认可;但是我国《仲裁法》仅认可机构仲裁,直至2016年12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为自贸试验区建设提供司法保障的意见》才开始尝试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内探索临时仲裁。然而,在我国境内作出的临时仲裁裁决与在境外作出的临时仲裁裁决,法律效力不一样:境内作出的临时仲裁裁决必须通过仲裁机构的转化才能在法院进行司法审查;根据《纽约公约》及我国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境外临时仲裁裁决可以直接在我国法院进行司法审查,无须通过仲裁机构的转化。在长期司法实践中,我国对约定在境外通过临时仲裁方式解决争议的仲裁条款效力予以认可,对境外临时仲裁裁决予以承认和执行。因此,在当前机构仲裁与临时仲裁处于完全不同发展阶段,且对境内、境外临时仲裁裁决持差异化对待的情形下,应注意根据机构仲裁与临时仲裁的不同特点探索与商事调解的差异化协同发展机制。
总之,《新加坡调解公约》既为我国商事调解发展带来了契机,也提出了挑战。《新加坡调解公约》不仅影响商事调解本身,也对商事调解与其他纠纷解决机制的协同发展提出了新要求。特别是在《新加坡调解公约》与《纽约公约》并行的框架下,探索我国商事调解与商事仲裁协同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构建一套高效可行的、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的商事调解与商事仲裁协同发展体系,有助于充分发挥调解与仲裁各自的效能,最大限度实现调解与仲裁的优势互补,最大程度实现定纷止争,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和谐公正。
The Impact of the Singapore Mediation Convention on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Commercial Mediation and Commercial Arbitration in China
GONG Butan LIU Wenzhao
Abstract: The Singapore Mediation Convention, which will come into force on September 12, 2020, heralds a major innovation in the global commercial dispute resolution system and a milestone in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mediation. The promulgation of the Convention fills in the gap that the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agreements arising from mediation cannot be enforced in relevant countries or regions. The three conventions, namely, the Singapore Mediation Convention, the New York Convention and the Convention on the choice of Court Agreements, will establish an implementation framework for mediation, arbitration and judgment. The Singapore Convention will not only bring China opportunities as well as challeng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commercial mediation, but also have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mercial mediation and other dispute resolution mechanism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commercial mediation and commercial arbitration.
Key Words: the Singapore Convention; Commercial Mediation; Commercial Arbitration; Coordinated develop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