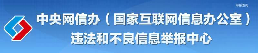编者按:“女书”在湖南省江永县潇水流域一带的部分女性中流传,既指女书文字,又指女书作品,有学者认为还应包括其吟唱。女书在20世纪80年代被誉为“一个惊人的发现”,激发了部分学者和公众的浓厚兴趣。但女书自清末以降已转向衰退,在正史、方志、族谱中未见记载,当地出土文物上亦无蛛丝马迹。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对其形成、流传、发展等问题未形成一致意见。
20世纪50年代,湖南邵阳的一个妇女被火车轧断了一条腿。她爬到医院,因说的话别人听不懂、写下的文字别人也看不懂,便被当做特务“请”到公安部门接受调查。她写下的文字形如“蚂蚁”、“蚊子”,不仅公安部门的鉴定人员闻所未闻,就连当时在中央民族学院(现中央民族大学)从事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研究的张公瑾、陈其光等人也无法辨识。这是女书第一次进入学者视野,但未引起足够重视。
女书作为一种书写系统在世界范围内都堪称独特。从《荷马史诗》到《格萨尔王》,口头传承在世界各地大量存在,但这些来自民间的说唱艺术,鲜有用文字记录下来的案例。在中国湖南江永县的大山深处,一群没有机会接受汉字教育的农家女,却用独有的女性文字记录下流传久远的民歌、故事。不仅如此,她们还为自己作传,书写乡村女性的个人史;创作结交老同书,寻找“灵魂”姐妹;制作精美的“三朝书”,向出嫁的姐妹表达最深切的祝福和思念。这些作品多为七言格律诗,偶有五言,不为阅读或私藏而写,而要同姐妹一起吟唱。女书文字、作品和吟唱构成了极具生活气息的女书文化,令国内外学者深深着迷。
女书起源于何时,是否为女性首创,有怎样的作用?带着这些问题,记者作了大量文献梳理,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中南民族大学的女书研究专家进行了交流,并采访了国内外相关研究者。日前,记者与前往江永进行女书田野调查的日本成城大学教授刘颖一起,走进女书流传之乡,拜访女书传人,探寻隐藏在女书符号背后的文化密码。
“草本”女书 建构女性精神世界
记者乘坐的列车驶入位于县郊的江永火车站时,已近夜里11点。车窗外是一片浓得化不开的黑色。走出车站,天空飘着小雨,这场雨淅淅沥沥下了8天。
江永县地处湘桂边界,四面环山,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县内有近200条河流蜿蜒流过。女书就在上江墟潇水流域两岸一些村子的妇女中流传。但即便是在这样小的范围内,也不是所有女性都懂女书。据说,十个人里,可能只有一两个会认、会写。
女书文字是世界唯一的女性文字(下文将女书文字称为“女字”),在正史、方志、族谱中未见记载,在出土文物上亦无蛛丝马迹,仅在1931年出版的《湖南各县调查笔记》中有如下记载:“每岁五月,各乡妇女焚香膜拜,持歌扇同声歌唱,以追悼之。其歌扇所书蝇头细字,似蒙古文。全县男子能识此种文字者,余未之见。”
女字被当地人称作“蚊形字”,字体修长圆润,呈长菱形,右上角高,左下角低,笔画有斜、弧、横、竖、点。关于女字的起源,由于缺乏材料,学界尚无定论,至今仍是未解之谜。但在族属和文字属性方面,有了较为一致的看法。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陈其光认为,女字记录的是一种汉语方言,是通过对近600个汉字的改造而来。由于改造方法多样,有些女字已看不出汉字原貌。作为汉字系文字,女字包含三个层次的变异:笔画变异、结构变异、形体变异。这种文字的书写有一定随意性,有很多异体字。依据不同的女书材料和评价标准,学者对于女字字数得出的结论相差甚远。陈其光认为,包括异体字在内,女字共有3000多个;日本文教大学教授远藤织枝认为有300—400个字;清华大学教授赵丽明认为只有100多个本字。
女字虽然是汉字变体字,但性质与汉字不同,是表音文字,用一个字符标记一组同音字。赵丽明认为,正是这种记录语言的特殊手段,使女书处在文字发展史的特殊位置。
女字的“文房四宝”颇有特色。据说,旧时上江墟妇女多用“棍子笔”蘸着锅灰在精致的布面、毛边纸、扇面、丝帕上写女书,分别叫做“三朝书”、“纸文”、“歌扇”、“帕书”,内容有原创性的贺三朝书、自传诉苦歌、结交老同书;有记录当地流传久远而又没有汉字记载的口头传统——民歌、祭祀歌、儿歌、传说等;还有改写自汉文的作品,如《祝英台》、《罗氏女》。
在江永县委宣传部的办公室里,宣传部副部长肖萍向记者介绍了他们田野调查时发现的三朝书合订本。“这是佚名作品,原来可能是四五本。书中有很美的图案。”肖萍说。
三朝书与当地贺三朝的婚嫁习俗有密切关系。贺三朝是指姑娘出嫁后的第三天,女方要向男方赠送抬盒三朝礼。抬盒中盛有女方亲朋好友馈赠的精美食品和三朝书,向新娘祝福,向男方恭贺。男方收到的三朝书越多,说明新娘越有教养。
女书多用来诉苦,尤其是自传。女书传人何静华在儿子去世后,用女书写下了诉苦诗文《悼逝儿》。“江永历史上是烟瘴之地,感冒发烧、口腔溃疡都会夺去人的生命。” 赵丽明说。女书诉的苦多是丧子丧夫之苦,如《中国女书集成》中收录的一篇自传写道:
念想行言提笔坐/我曰可怜诉一篇/我是九元年所生/七月生七月养的 可可怜怜养下地
亦没盐亦没油吃/念起停餐找饭吃/想起我身好可怜……
这篇自传诉说了主人公坎坷的一生,尤其表现了老年时的孤苦无依。
女书内容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大都不涉及对人类社会的深层思考,也没有描述人类起源的创世传说。透过女书作品我们可以看到,女书使用者是这样一群女性:她们在现实生活中受到儒家“三纲五常”的束缚,没有与男人平等受教育的机会;但也有相对自由的空间,一般不下地劳作,往往与女伴一起做女红、唱女书,空闲时或一起或独自创作、吟唱、玩味女书。祭祀、坐歌堂、看戏等习俗和活动,是她们创作灵感的重要来源;江永女性专属的吹凉节、诛鸟节、斗牛节等,则为女书提供了成长的空间。这种文字以老传少、母传女的方式代代相传。
女书文本注定在历史上只会昙花一现。当地有“人死书焚”的习俗,女书文献无法稳步积累或世代相传,被学者喻为“草本植物”,女书老人阳焕宜2004年去世时,就烧掉了近1尺高的女书作品。
江永县潇浦镇历史上并没有女书流传,但如今,女书在当地已是家喻户晓。随着女书被发现,不仅出现了一批学术成果,而且还出现了与之相关的小说、电影。为保护、宣传女书,江永县建起了女书生态博物馆和女书数字博物馆。女书生态博物馆建在女书流传的核心村上江墟镇蒲尾村,那里是已故女书老人高银仙、胡慈珠、唐宝珍的故居地,现有五位女书传人在博物馆工作。
故地寻踪 聆听女书“声音”
在淅淅沥沥的小雨中,记者与刘颖在县委宣传部陈军的带领下,乘出租车前往蒲尾村。在接下来的五天里,记者一行到河渊村看望女书传人何艳新;走访已逝女书老人义年华生活过的桐口村、传说中的女书创造者胡玉秀的家乡荆田村;探访女书曾活跃过的花山姑婆庙、道县龙眼塘娘娘庙。
蒲尾村完整保留了女书文化的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走在村里,有现代和历史交错的奇妙之感。沿村内潇水支流弯曲延伸的水泥路一侧,旧房与新房交错,路边停有摩托车、小汽车。在另一侧河水静悄悄地流淌,渔人泛舟其上,一群鸭子畅游其中。一排两层的古建筑倒映水中,那是村里的古街市,曾热闹非凡,现已废弃。
村里的女书园是记录、储存女书文化的资料中心,设有女书书画厅、作品厅、女红厅、工艺品展销厅和女书学堂,通过实物、文字、图片、音像等形式,展示女书原件文献、作品、工艺、书法和学术研究成果。虽然地处偏远,仍有不少游客慕名而来。
在女书书法演示厅里,前来参观的江永县一中学生张开船认真地摹写女字;华中农业大学的研究生胡鑫在电视上看到关于女书的介绍,爱好书法的他误以为女书是与楷书、隶书并列的书法字体,便从武汉前来参观。当他得知女书是一种文字时,甚感惊讶。他对记者说,女书很漂亮、很特别,极具地方文化底蕴。
在第三展厅女书陈列馆里,从展示的1982年《本县上江圩镇末代女书自然传人调查表》上可以看到高银仙、义年华、胡慈珠、唐宝珍、阳焕宜等已故女书老人的名字。她们自称“君子女”,生前受学者之邀写下大量女书作品,配合学者做了大量翻译和唱读录音工作,为抢救女书作出了重要贡献。
阳焕宜生前曾对学者说:“他们(男人)是君子,我们是君子女;他们有男字(汉字),我们有女字;男字在书桌上写,女字在膝盖上写。”简单几句话,勾勒出女书的独特所在。随着女书老人们的离去,现在很多作品难以释读,成了永远的秘密。
我们还去河渊村访问了另一位女书传人何艳新,她曾多次受邀到国内外很多地方参加女书学术研讨会,写女字、唱女书、解答与会者的疑问,为女书的传播和研究做了大量工作。在采访何艳新时,她还给我们唱女书,并展示她参加各种女书活动的照片。
女书听起来很古朴,只是一种简单调子的重复,没有歌曲那样丰富的旋律。刘颖说,女书按当地优势语言城关土话的七个声调“依字行腔”,以一对上下句为单位依次吟唱,上句(奇数句)尾字可用城关土话中任何一个声调的字,下句(偶数句)韵脚一定要押城关土话的阴平44调和阳平42调。
关于女书的口头表达方式,学者有不同的叫法,如吟诵、吟咏、读念、咏叹等。刘颖告诉记者,她调查过的女书老人都是吟唱着识读女字,吟唱着玩味内容,吟唱着创作作品;老一辈女书传人吟唱着传授晚辈,晚辈也是吟唱着学习与记忆。但除了吟,女书还有唱的要素,通过近十年的记谱分析,她发现女书有固定的曲调,基本音阶有3个,女书传人自己称为“高调”、“中间调”和“低调”。
女书直接或间接地改变着村民的生活,女书传人对此感受尤甚。目前,最年轻的女书传人胡欣生于1987年,她告诉记者,因为女书,她有了经济来源,而且结识了全国各地的朋友。2011年11月24日,她与另一位传人胡美月一起参加了在台湾举办的“第二届两岸非物质文化遗产月”活动。
女书研究 三十年甘苦路
20世纪50年代,邵阳女子的偶然遭遇使女书得以走进国家级研究机构,但却没有引起专家学者的注意。60年代“破四旧”,女书从妇女们的生活中消失,处于濒危状态。直到1982年,中南民族学院的宫哲兵偶然发现女书,深入调查后于1983年发表了《关于一种特殊文字的调查报告——湘南瑶山采风记》一文,女书的生命才得以延续。
1983年,时任中南民族学院副院长的语言学家严学窘与宫哲兵合作撰写《湖南江永平地瑶文字辨析》,提交在美国召开的第十六届国际汉藏语言学会议,引起了国际汉藏语言学家的兴趣。美国语言学家哈里·诺曼教授在写给严教授的信中说,女书是一个惊人的发现,它将引起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的极大兴趣。
随后,来自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外研究机构以及清华大学、中南民族大学、台湾“中研院”的专家学者,陆续到江永各村调研,研究由此深入展开。虽然学者们的研究角度不同、某些观点分歧较大,但对女书的价值都给予了充分肯定。
美国学者史凯姗1988年曾在桐口村向义年华学过半年女书,她用人种学方法来研究文化。得知本报在考察、报道女书,她非常激动,立刻回想起30年前为完成博士论文在江永田野考察的往事。她告诉记者,女书这一女性传统在世界范围内也非常独特,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应给予足够的关注。
赵丽明是早期研究女书的学者之一。她的五卷本《中国女书合集》是目前有关女书研究最全的资料汇编。她告诉记者,上世纪80年代寻找到的女书传人都是“三寸金莲”,女书文化本质上是汉文化的一个支系,但不能单纯地判断女书是汉族的还是瑶族的,应该说是中原文化和南方文化交融的产物,是汉风瑶俗的混血儿。
远藤织枝20世纪90年代开始从女性学角度考察女书的价值,至今已经出版了《中国的女文字》、《中国女书研究》等论著。她认为,三朝书和自传是女书中最具女性学研究意义的作品。
刘颖的关注重点是女书的吟唱。她认为吟唱是女书传承极为重要的部分,并由此展开了深入细致的调查。她发现,过去女书是在自然环境下习得,学唱容易、学写难;而当今的女书传人则学写容易、学唱难。这是因为女书传人有汉字基础,因此学写女字容易,但失去了歌堂文化环境,所以学唱难。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有一部适合的“女书吟唱教科书”。这需要研究女书吟唱的规律,总结其中的规则,而这也正是她研究女书曲调规律的意义所在。
学界近30年的女书研究取得了大量成果,资料整理和调查笔记翔实。但由于原始资料缺乏、女书研究时间尚短,诸多问题有待深入研究。失去使用价值后的女书更多是为学者提供研究资料,为书法界提供素材。女书还被江永县列为旅游开发的重点项目。学者们认为,女书进入了“后女书时代”。赵丽明说:“从这个意义上讲,女书永远不会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