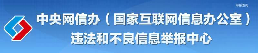社会第一站(外四章)
作者:陈汉临
那是1975年的初秋,“双抢”的暑气还未散尽,田埂上堆着新割的稻茬,空气里混着泥土和秸秆的气味。一个刚满十八岁的我,被一纸调令抽调到公社工作队,背着一床薄被和几件换洗衣服,走进了青菱公社的毛坦大队。这里,便是我踏入社会的第一站。
大队部是几间低矮的瓦房,工作组六个人,挤在一间办公室里。组长是公社党委副书记王才东,一位面色黝黑、身板墩实的中年人。他分配任务时,总是带着浓重的花山乡口音把工作组的任务、目标说得清楚明了。那时,全国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刚开过,复出的邓小平副主席作报告的声音,通过层层传达,仿佛还在我们这些基层农村工作队员的耳畔回响,激励着我们投身于那场轰轰烈烈的农业学大寨、改天换地的热潮。
我住进了四队队长陶银州的家。他家是三间简陋粗糙的红砖瓦房,这在毛坦村算得上是比较好的房屋,还有很多土砖茅草屋。晚上,我睡在一个废弃的、用来装谷物的木柜子上,翻身时,木板嘎吱作响,谷物的尘屑和干燥的木香便丝丝缕缕地渗入梦里。吃饭是“派饭”,一天轮一户。我揣着一天四毛钱、一斤粮票,从村东吃到村西。煮饭的的鼎锅冒着热气,里面一半是红薯一半是米饭。乡亲们把好一点的菜往我碗里夹,那淳朴的、带着些许局促的笑容,让我心里既暖又酸。我们和社员真正是“同吃同住同劳动”。
当年的秋冬,为满足全市“菜蓝子”供应,公社决定把种植水稻的大队全部改为种植蔬菜。于是我们便和社员一起,抢收完最后一季稻谷,然后挥起锄头,挖沟开槽,把水田改造成菜地。
晚上,政治夜校的灯火在生产队的队屋里亮起。由我这个最年轻的队员负责,给社员们读文件、念报纸,传达上级关于“批林批孔”、“评法批儒”的最新指示,也协肋队长强调明天的生产任务。灯光昏黄,映着一张张疲惫而专注的脸。最热闹的是评工分的时候,“自报公议,死级活评”,有人高声自荐,有人小声嘀咕,烟火气与生存的计较,在小小的屋子里弥漫升腾。
然而,外面的风似乎变了向。工作队进驻时说的“三年”,到年底就传来了结束的消息。隐隐约约听说,是上面的邓副主席又出了问题,“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风声紧了,我们这场“农业学大寨”的运动,便也像断了线的风筝,草草收场。
离开那天,大队开了欢送会。一些相处了数月的社员拉着我的手,絮絮地说着告别的话。一位老贫协主席,手像粗糙的树皮,紧紧攥着我的手,声音有些发颤:“你要不走,留在这里当队长就好了……”那一刻,我喉头哽咽,所有关于运动和路线的宏大叙事,在具体的人与质朴的情感面前,忽然变得遥远而模糊。
我背着来时的行囊离开了毛坦。身后,是依然贫困的村庄,是那些简陋的矮房,是鼎锅里翻滚的红薯米饭。
几年后,十一届三中全会像一场春雨,土地承包了,村办企业如春笋般冒了出来。乡亲们的口袋鼓了,生活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发生着巨变——土房变成了楼房,自行车换成了摩托车,后来又变成了小汽车。进入新世纪,城中村改造,他们彻底告别了世代耕耘的土地,住进了整洁的居民区,老人领着养老金,年底还有股份分红。
我常常想起那段岁月。那是我社会的第一站,它让我在最朴素的劳作与最基层的生活中,触摸到了中国的真实脉搏。我们当年怀着理想主义激情想要改变的贫困,最终并非由我们那场草草收场的运动所终结。历史的车轮,自有其更深刻、更符合规律的轨迹。我们那一代人的青春,连同毛坦村的鼎锅、木柜、政治夜校的灯光,都已成为那个特定年代的注脚,封存在记忆里。而真正让那片土地和人民获得新生的,是后来那场回归常识、尊重人性的伟大变革。
那社会第一站的酸甜苦辣,如今品来,已滤掉了当年的迷茫与困顿,沉淀下的,是对一段纯粹时光的怀念,以及对脚下这片土地与人民最深沉的祝福。
11月6日写于青菱湖畔圆梦园农庄
我的少年时光
我今年六十八岁了,退休也有八年。人一闲下来,就总爱回想过去的往事。我的思绪常常会飞回老家老桥村,飞回那段泡在湖水里的少年时光。
我的老家,村子东边是风光旖旎的青菱湖,西边是玲珑剔透的野湖。那时候,这两个湖就是我们这群孩子的乐园。夏天一到,湖边上密密麻麻长满了莲藕和菱角。一放学,或者放了暑假,我们几个小伙伴就成天泡在湖水里,抽藕带,采菱角,摘莲篷。那时候不觉得是在干活,只觉得是天底下最好玩的事。
等到冬天,湖水退了,湖底露出大片的淤泥。我们又不闲着,卷起裤腿,光着脚丫,就去掀泥挖藕。虽然是寒冬时节,但那时候哪知道冷啊。有时候,我们还会钻到枯黄的蒿草丛里,寻找鸟窝,偶尔能掏到几个鸟蛋,那就像发现了宝贝一样。
那时候,农村的日子过得紧巴巴。家里穷,每到开学,学杂费和买书本文具的钱,就成了家里的一件愁事。但我们这些半大的孩子,已经懂得为家里分忧了。
夏天天不亮,我们就用扁担挑着采摘的莲蓬,走上很远的路,赶到长冮边的石嘴码头,乘坐那种“突突突”响的轮船,摇摇晃晃地到汉口去。在汉口的街巷里,我们不敢象大人一样吆喝,只是静静的守候在箩筐旁。一个暑假下来,靠着这小小的生意,竟然能挣上几十百把块钱。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了!交了学费,买了文具,还能剩下一些补贴家用。手里攥着自己挣来的钱,那份自豪感,到现在都还记得。
读初中时,我们每天只上半天课。下午,我们就跟着生产队的大人们一起下地劳动。村里四五个年纪相仿的伙伴在一起,一边觉得好玩,一边也想着为家里多挣几个工分。那时候我们力气小,干半天活,只能记三个工分,虽然不多,但心里是满满的成就感。
后来上了高中,个子长高了,力气也大了,心里就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头。星期天参加队里劳动,专挑重活干。比如挑“谷草头”(捆好的稻谷),队里的男劳力都是挑双担(前后各两捆),我们这些学生娃也咬着牙,晃晃悠悠地挑起双担,硬是要跟他们比一比。一天下来,肩膀压得又红又肿,心里却觉得有一种自豪感。
现在回头想想,我读书的时候,正赶上文革,学校里上课很轻松,很多文化知识学得不系统。但那段岁月,也让我在另一个课堂里学到了很多。我认识了脚下的土地,熟悉了湖水的脾性,学会了怎么种地、怎么收获,更懂得了生活的不易和劳动的光荣。这些从泥土和湖水里学来的知识,同样让我受益终身。
如今,青菱湖和野湖已经变了模样,但那段在水里泥里打滚、靠着自己双手挣学费挣工分的少年时光,却像刻在了心里,永远那么清晰,那么鲜活。那不仅仅是一段回忆,更是我人生里最宝贵、最扎实的根基。
11月26日写于青菱湖畔圆梦园农庄
父亲
我的父亲陈幼龙离开我们已经十八年了。每当夜深人静时,他的音容笑貌总会浮现在我眼前。
1936年9月1日,父亲出生在一个普通农家。那时家里有十几亩田地、三间瓦房,日子还算宽裕。他因此得以读了两年私塾,这在当时已是不错的启蒙教育。
可惜好景不长。村里开了家茶馆,实为赌场。祖父沉迷其中,不仅输光了积蓄,还欠下不少赌债。祖母常说,每年粮食刚收完,讨债人就挑着箩筐上门,把大半粮食都挑走了。剩下的粮食不够吃,她只好去给人家帮工,换些米回来糊口。父亲的童年,就在这样的困顿中度过。
解放后土改,因家产早已败光,我家划为贫农。1958年,父亲参加"大办钢铁",到黄冈当矿工。三年困难时期,城市精简人员,父亲又回到农村。不久,父亲因有点文化,又积极上进,组织上培养他入了党,又安排他当上了生产队队长。
这个小队长一当就是二十多年。生产队长看似官小,却关系着全队三十多户、一百多口人的生计。春耕秋收,都要他安排调度。父亲很有远见,六十年代带领大家在荒山种桃梨,七十年代改种柑橘,改革开放后又改种莲藕、芋头等经济作物,总想方设法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
在家里,他要养活我们兄弟姐妹五个。长期的劳累让他落下病根。先是得了肾炎,那时农村医疗条件差,他每次都要步行到石嘴镇,再坐车去城里看病。买不起盐,只能吃代盐,这对一个干重活的人来说真是雪上加霜。1971年他又患上肺结核,幸亏一位知青把他父亲的药分给父亲吃,才慢慢康复。
改革开放后,我们陆续成家外出,家里只剩父母相依为命。母亲体弱多病,农活主要靠父亲。2007年,他的肾病复发转为尿毒症。虽经一年治疗,终因多器官衰竭,在2008年5月22日永远离开了我们,享年72岁。
父亲这一生,经历了太多苦难,但他始终坚韧不拔。他用自己朴实的行动,教会我们什么是责任,什么是担当。他就像一头老牛,默默耕耘,无怨无悔。这多年来,我常常想起他说的那句话:"人这一生,不求大富大贵,但求问心无愧。"
父亲虽然离开我们18年了,但他的精神和品德却永远在我们家族中延续。
11月29日写于青菱湖畔圆梦园农庄
车城之恋
我和许银枝是同一个村长大的,老家叫老桥村。仔细算起来,两家还是远房亲戚,只是平时来往不多。我们从背着小布包上小学,一直到高中毕业,几乎天天见面,可那时候年纪小,谁也没往别处想。
1976年春天,银枝的父亲因公去世,她接过父亲的班,去了十堰市的东方食品厂工作。一下子,我们之间隔了山又隔了水。直到第二年,我才鼓起勇气,给她写了第一封信。信里聊了些工作上的事,也悄悄写了几句心里话,告诉她我一直很佩服她。可信寄出去后,却象泥牛入海,一点回音也没有。
我心里有些失落,但也只好把这份心思放下。1978年春,我正式参加了工作。没想到那年年底,一个同乡突然转给我一封信——竟是银枝一年前写给我的回信!原来那时候乡下寄信收信都不太规范,这封信在大队部一躺就是一年多。
信上说,她刚进厂,想先安心工作,个人问题等一年后再考虑。可等我读到这封信,都快两年过去了。我赶紧又给她写了封信,她也很快回信,说愿意相处。那年春节她回老家,问了母亲和哥哥姐姐,家里人都没意见,我们这才正式确定了关系。
从那以后,我们开始鸿雁传书。我们在信里谈工作,谈理想,也悄悄规划着未来。薄薄的信纸,承载着我们沉甸甸的思念。
1979年春天,我突然收到她的信,说得了阑尾炎,动了手术。我立刻向单位请了假,连夜坐上火车赶往十堰。那是我第一次去十堰,天刚蒙蒙亮就下了车,一个人在陌生的城市里打听问路,好不容易才找到东方食品厂。
见到她才知道,手术出了点意外,麻醉药渗到了硬膜外,导致她走路不稳,晚上还怕光。我心里揪得紧紧的,立刻陪她去医院继续治疗。那段时间,我看着她慢慢好转,心里才踏实了些。
后来银枝告诉我,厂里有个石家庄来实习的小伙子,对她挺有好感。不过她说,心里已经装了一个老家的小伙子,再容不下别人了。听了这话,我心里暖暖的。
两年的隔空往来,让我们的心越靠越近。到了1981年底,我们都到了该成家的年纪。1982年元旦,我们简单办了婚事。婚假结束后,她又回了十堰,我们开始了新婚即分居的日子。
同年10月25日,我们的孩子出生了,给我们带来了无尽的喜悦。但真正让我们安心的是第二年秋天——在区委组织部部长的亲自关心下,银枝终于调回了武汉。
从此,我们结束了牛郎织女生活,开始了人生新的里程。
11月30日写于青菱湖畔圆梦园农庄
我与洪山新华书店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由于工作关系,经常要到区委区政府开会。每次开完会,我总会不自觉地往街道口走——那里有家洪山新华书店,成了我那些年里最常去的地方。
那时的书店很大很宽厰,两层楼,书架上挤得满满当当。柜台上摆着新到的图书,用硬纸板写着推荐语。我尤其喜欢文学和社科类的书架,常常一待就是半天。那时工资虽然不高,但每个月总要挤出一点钱来买书。
有两件事我至今记得清清楚楚。
1997年12月24日,我记得那天特别冷。我照例去书店转转,没想到门口排了长长的队伍。一问才知道,是著名相声演员牛群来签名售书,卖的是他的摄影集《牛眼看家》。我也跟着排了进去,队伍挪得很慢,但没人抱怨。轮到我的时候,牛群笑着接过书,然后在扉页上用签字笔签上草写的“牛群”二字。那本书我到现在还收藏着。
另一回是1999年7月18日,正是武汉最热的时候。书店里人山人海,女作家王海鸰在签售她的畅销小说《牵手》。队伍从二楼排到一楼门外,在七月的太阳下弯弯曲曲。我汗流浃背地排了一个多小时,终于拿到了签名本。王海鸰很有耐心,对每个人都会说:“谢谢您喜欢这本书。”那语气很柔和,然后工工整整地签上名字和日期。
后来城市变了样,街道口越来越繁华,高楼一栋栋立起来,洪山新华书店却由于商业化逐渐宿小了。后来虽然我还是会偶尔去看看,但总觉得少了点什么——也许是少了当年那个挤在人群里、小心翼翼翻开新书的自己。
那些在洪山新华书店度过的午后,那些排队等待的签名,那些用牛皮纸包好的新书,构成了我生活里最朴素也最充实的一部分。书店不仅仅是卖书的地方,它是一代人精神的驿站,让我们在平凡的生活里,能够暂时停下脚步,与更广阔的世界相遇。
2025年12月8日写于青菱湖畔圆梦园农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