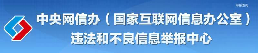一封未寄出的家书
作者:王冠中
每年八月第一周,我擦拭黑管的指腹总会停在第七键。这个键比其它键明亮许多,那是经年累月泪水的冲刷,四十多载光阴里,酸涩的泪痕默默打磨着铜键,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如同岁月默默雕琢着记忆的印痕。

一九八零年七月末,我们文工团前往张家口宣化靶场慰问演出,那年,我十六岁,怀揣一支木制黑管,也揣着少年人初次远行的兴奋与新奇。母亲在武汉,六辆大交通车启动前,我匆匆写了一封家书:“妈,任务结束就回,北京稻香村的点心给您带!”满眼望去没有邮筒发出,那字迹带着少年特有的飞扬,却成了日后永远无法兑现的诺言。
靶场深处,沙尘弥漫,空气里弥漫着燥热的火药气味。我们在临时搭起的简易舞台上,为刚刚完成演练的战士们演出。当精彩的节目出场,我的黑管声与战友们的小号、手风琴声一起伴奏、热烈迸发。台下战士们黝黑的面庞上,汗珠在烈日下闪烁,他们那热切的眼神和响亮的掌声,仿佛一阵阵灼热的风扑面而来。曲子行进到最高昂的段落,我忽然心口一悸,仿佛被无形之手攥住,喉头莫名哽住,黑管发出一声几不可闻的岔音,旋即淹没在宏大的乐声里——那瞬间的失序,成了命运提前投下的一缕不祥阴影。当时我未曾多想,只当是暑热难当,或是自己技艺尚需锤炼。
演出结束,我们随即乘上返回北京的汽车。一路颠簸中,我还不知道,就在我随乐声昂扬起伏的当口,数千里之外,母亲那晚突然从央视新闻报道中看到了我正在演出,当晚疾病复发,抢救无效,永远离开了她时刻惦念的小儿子!
当车队终于抵达北京,我心中还盘算着何时能请假回家,向母亲炫耀靶场演出的荣光。回到文工团驻地,暮色已然四合,晚风拂过燥热的空气,我拖着疲累的身体正要回宿舍,值班室的战友急匆匆奔了出来:“快,团长让你去趟办公室!”
一推开门,文工团长神情凝重,嘴唇微微翕动,犹豫片刻后,终于递来一张薄纸片。纸片是电报,上面寥寥数字却如寒冰刺骨:“母病故速归”。
我全身僵直,电报上的字迹如墨汁流淌,瞬间浸透了我整个认知世界。大脑仿佛瞬间被抽空,只剩一片混沌的空白。我甚至忘了自己是怎样机械地挪动脚步,又是如何木然地办理了手续,只记得团长低沉的声音在耳畔嗡嗡作响,每一个字都像沉重的锤子砸在我心上。我记不清自己如何收拾行李,只觉一股冰冷的窒息感由心脏蔓延至指尖,如坠冰窟。
我登上了南下武汉的37次绿皮火车,车轮在铁轨上滚动,发出单调而沉闷的轰响。我蜷在硬座车厢的角落,未饮一滴水,未进一粒米,眼睛死死盯着窗外不断更迭的风景,却什么也映不进眼底。窗外景象飞速后掠,如同我心中那截然断裂的时光隧道,再也无法返回。我在心中反复咀嚼着母亲可能弥留之际的每一点念想:她是否在呼唤我的乳名?是否在埋怨儿子的缺席?她最后的目光,是否在门口徒劳地张望……这些念头如烧红的铁针,反复刺穿我虚弱的神经。我甚至不敢合眼,怕在梦里错过母亲在另一个世界的呼唤。
终于抵达武汉,我跌跌撞撞扑向家的方向。家门紧闭,邻居闻声出来,带着不忍的神情告诉我:“你妈……前日已经入土了。” 我深一脚浅一脚来到郊外的新坟前,坟头黄土尚新,几丛野草刚刚探出怯生生的头,旁边散落着几颗干瘪的莲子,那是母亲生前最爱之物。我双膝一软,重重跪倒,额头抵在冰冷的泥土上,失声痛哭。手指深深抠进坟头的新土,指甲缝里嵌满了泥土,恍然间,指尖竟摸到些许熟悉的、硬硬的沙粒——那是宣化靶场粗砺的黄沙,演出时沾染在军裤上,一路带回北京,又随我跋涉千里,最终混入了母亲坟头冰冷的土壤。这相隔千里的风沙,竟以如此残酷的方式在母亲的安息之地相遇了。
我颤抖着双手,从贴身口袋里掏出那没有发出的家书,字迹已被汗水晕开:“妈,任务结束就回,北京稻香村的点心给您带!”纸页在风中簌簌抖动,像一只垂死的蝶。我点燃火柴,家书在坟前化作一缕轻烟,带着点心香甜的许诺,飘向母亲再也无法品尝的虚空。火舌舔舐着纸页,如同舔舐着未及实现的承诺,灰烬飘散,像一场无言的诀别雪。
那一年,十六岁的夏天,宣化靶场的风沙与武汉郊外坟头的黄土,以最残忍的方式在我生命里刻下了永久的界碑。从此,我所有的归途都指向一座沉默的坟茔,而那个曾经可以奔赴的家,永远停在了地图之外。
母亲走后,我生命里那个名为“归途”的锚点永远沉没了。我依然在文工团吹奏黑管,音符成了我唯一能安放思念的容器。当黑管声响起,我似乎总能听见母亲温柔的回应;当乐声停歇,巨大的沉默便如潮水般涌来,将我淹没在无边的寂寥里。那截被泪水反复打磨的第七键,是我生命刻度上永久的伤疤,也是我与母亲之间无法切断的、无声的交谈。
今天,又到了八一,我来到内蒙包头,颤抖着写下:
《给母亲》
1980年的夏天,武汉的蝉鸣比往年更刺耳。
在您生日这天,
您把自己还给了时间。
那时我在北京某文工团当兵,
天黑管的木质被晒得发烫,
指间漏走的音符,
像您梳子下断落的银丝,
再也没能接回。
他们说癌痛如刀,
可您走时,
却把的确良衬衫熨得平整,
连最后一粒纽扣,
都系得端正。
四十五年过去,
我仍会在8月1日擦拭黑管,
松香落在琴键上,
想起您总跟我说的:
“毛毛,你要好好吹黑管,好好的做军人!
而今我终于明白,
您不是放弃,
只是把疼痛,
换成了永恒的安静。
我会永远怀念您,我伟大慈祥的母亲.
(写于母亲逝世45周年忌日)

这世间最遥远的距离,原来并非千山万水,而是我还在舞台中央,您却已不在观众席上;是那封塞进邮筒的家书,永远寄达不了您已阖上的眼帘。